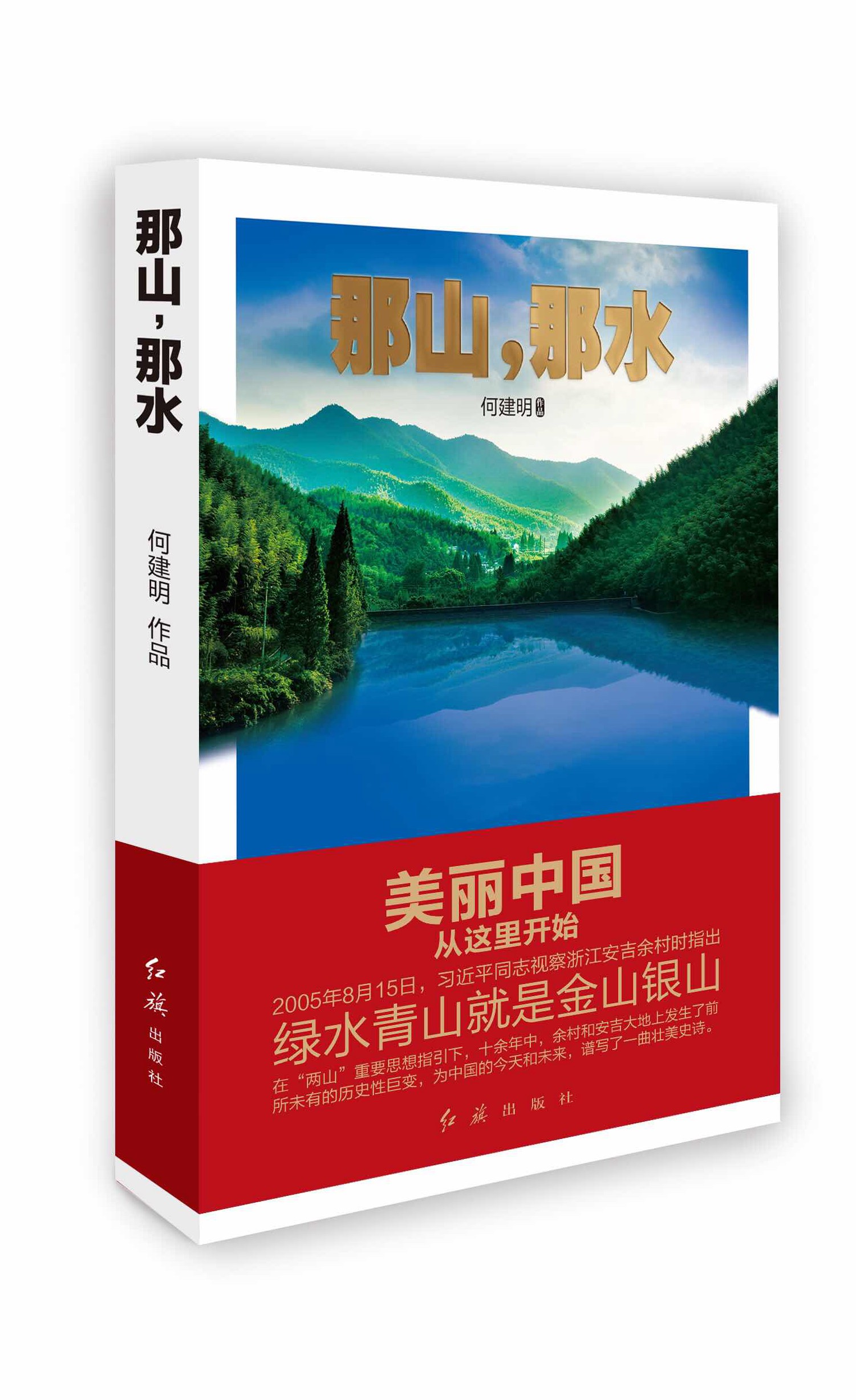《那山那水》 拾贰
2018年01月17日 15:41 《那山那水》 何建明
其实,余村百姓的话代表着多数中国人的真实心愿。难道那些已经很富裕的上海人、北京人和深圳人内心不是这样想的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在余村,在安吉和浙江大地上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朝气、前景无限的美丽新时代,就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践上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紧扣了一切发展以人民利益为核心这一根本。
古人曰:“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民而不扰民为本。”自然较之人,人顺自然则为本,人扰自然则为弃本。为本者昌顺,弃本者逆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的是人类昌盛、繁荣、强大和不灭的一个真理,故而在中国和全人类发展遇到新挑战、新岔口时,它犹如一道刺破万丈迷雾的光芒,给中国和整个人类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和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力。
看一看安吉这近十余年来的巨变,我们就清楚了“两山”重要思想的威力。
唐中祥,现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2005年年初,这个“秀才”出任安吉县代县长、县长。之前,他的职务先后是湖州日报社社长、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是个典型的“笔杆子”。到安吉县的第二年,唐中祥出任县委书记,一直到2011年。用安吉人的话讲,这是他们在习近平“两山”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推进从“绿水青山”转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性历史阶段。
说其“关键”,是因为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过程,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社会发展中的认识能动过程,都非一日之功,而且这一过程充满着事物之间的种种矛盾,甚至是尖锐的斗争。
“安吉人重视绿水青山并非现在的事,历史上早已有之。旧县志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其岭峻绝,修竹苍翠,拂人衣裙。自南宋至民国时期,历代官府发布的‘护林’‘禁伐’令不下数十个,民众护林爱竹者更不知其数。但旧时的‘护林爱山’只是出于人们对这一片生养自己的土地的自然情感。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安吉真正进入了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一方面是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各种对物质生活渴求的思潮洪流般地涌入城乡,搅乱了山村的宁静;另一方面是长期生存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急切想改变现状,恨不得拿自己的母亲河、祖宗山去尽快变现的欲望,而短视的结果就是到处乱砍滥伐、开矿山,不计代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所谋求的生活改善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到底是要金山银山,还是要绿水青山,成了一对矛盾体。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体,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和实践活动。谁来破解这一命题,谁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便成为当时一村一县甚至一市一省发展的关键点。习近平同志就是在我们当时面临的发展这个关键点上,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英明论断,为处在矛盾焦点上的我们指明了方向。这才有了余村,有了安吉甚至整个浙江后来十多年的根本性变化……”唐中祥说。
“其实,无论是余村,还是整个安吉,在处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矛盾关系时,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比如,我刚到安吉,记得当时财政局提供的数据是,安吉全县财政收入才六七个亿。这是2005年的时候呀!我们安吉处在杭嘉湖地区,那时像萧山早就是超百亿的全国‘百强县’了。太湖对岸的苏州下辖的几个县更了不得,他们财政收入的零头都比我们一年的财政还要多得多,像华西一个村的财税就超过了我们安吉全县。可安吉为什么这么少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一阶段我们正处在既想要绿水青山,又想要金山银山的困惑中,结果经济出现了暂时性的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还很大。堂堂一个县级政府,没了钱,缺了钱,这样的领导有多难当!百姓对你也不会满意。所以,当时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我这个当县长、第二年又当了县委书记的安吉‘一把手’,压力自然更大了。”唐中祥说:“那时我天天夜里两三点还不睡,一个人蹲在床铺上看报表,第二天再找各个部门负责人来开会,分析问题,寻找发展的出路……”
“在讨论和研究过程中,有人对我说:安吉的GDP也曾不错过,后来是因为不让乱砍滥伐乱开矿了,所以财政收入就降了下来。开会时我对大家讲,安吉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关键的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真正富起来。而安吉的经济要搞上去,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再高的GDP,再多的财政收入,也不能给百姓和安吉带来真正的幸福与美好。但说心里话,当时我倍感压力的是,一方面你要发展但又不能去破坏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你不办工业、没有产业又无法把经济搞上去,两难哪!如果没有财政收入,公务员的工资你能降吗?肯定不会有人举手表示同意的。大家都希望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百姓更想看到生活比以前越来越好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也很正常。”唐中祥分析道,“安吉包括余村在内,最初的发展大家也都怀着这样的愿望,为了摆脱贫困,想方设法寻找各种可能去发展经济。安吉过去是浙江省20个贫困县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无工不富’的浪潮影响下,安吉也走了一条靠山吃山的发展路子,这过程一直到1998年国家实行‘太湖零点行动’止。那一阶段,安吉地面上到处是冒烟的小矿、小厂,污染极其严重,砍竹开山,卖竹卖石头赚钱。钱确实也赚了点,但环境破坏得太严重了,连老百姓自己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一阶段,我们称它是‘宁肯要金山银山,也不要绿水青山’,结果是金山银山没有真正要到,只见了些碎金碎银,既没让百姓富起来,也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我们的绿水青山也被严重损毁了。”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太湖零点行动’,至2005年左右。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我们既想要金山银山,也想要绿水青山的时候。”唐中祥感叹道,“这个过程特别痛苦。因为财政收入下降了,上上下下忧心忡忡……”

生态绿带绕县城 夏鹏飞 摄
唐中祥说的“太湖零点行动”,是国家为了实现“2000年太湖水变清”“不让污染进入21世纪”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污染治理战役,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98年年底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并在1999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宣布“基本实现阶段性的治理目标”。一
国家有关部门之所以投入百亿元的资金,进行一次如此声势浩大的针对太湖水染污治理采取的大行动,是因为80年代之后的十几年间,苏南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发展太快—根本不讲究环境保护,尤其是不讲究水质保护。水对江南水乡而言,是人们生产与生存的根本,太湖之水涉及和影响到周边4000多万人口的生存,太湖水污染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人们就等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中国还有希望吗?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不可再延缓一分钟的时刻。国家无奈,以“零点行动”的方式,对那些污染太湖水的企业实行强制性的关停并转。当时采取的措施十分严厉,具有强制性和时间性。所谓的“零点达标”,就是要求在1998年年底,太湖地区的1035家重度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这1035家企业中,江苏省占770家,浙江省占257家,上海市占18家。安吉的西苕溪污染列在其中。
“太湖零点行动”,对江浙沪两省一市的许多企业和党政机关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也是他们把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划分点定在“太湖零点行动”上的原因。
“太湖零点行动”,给安吉的发展画上了一道深深的历史界线—从此,既要金山银山又要保护绿水青山,成为安吉发展的主旋律。
“但后来发现,这种既想要熊掌,又不舍得丢鱼的发展思路是很难实现的。于是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些企业,要么偷偷地排污,悄悄地走老路;要么遵命听令,等着经济指标一滑再滑,滑到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工作最难做,利益冲突也前所未有地显现出来了!但是再难,安吉历届县委、县政府坚持生态立县的意志和信心从没有动摇,这一点确实令人敬佩。”作为这一阶段的继任者,唐中祥言语间流露出对其前任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