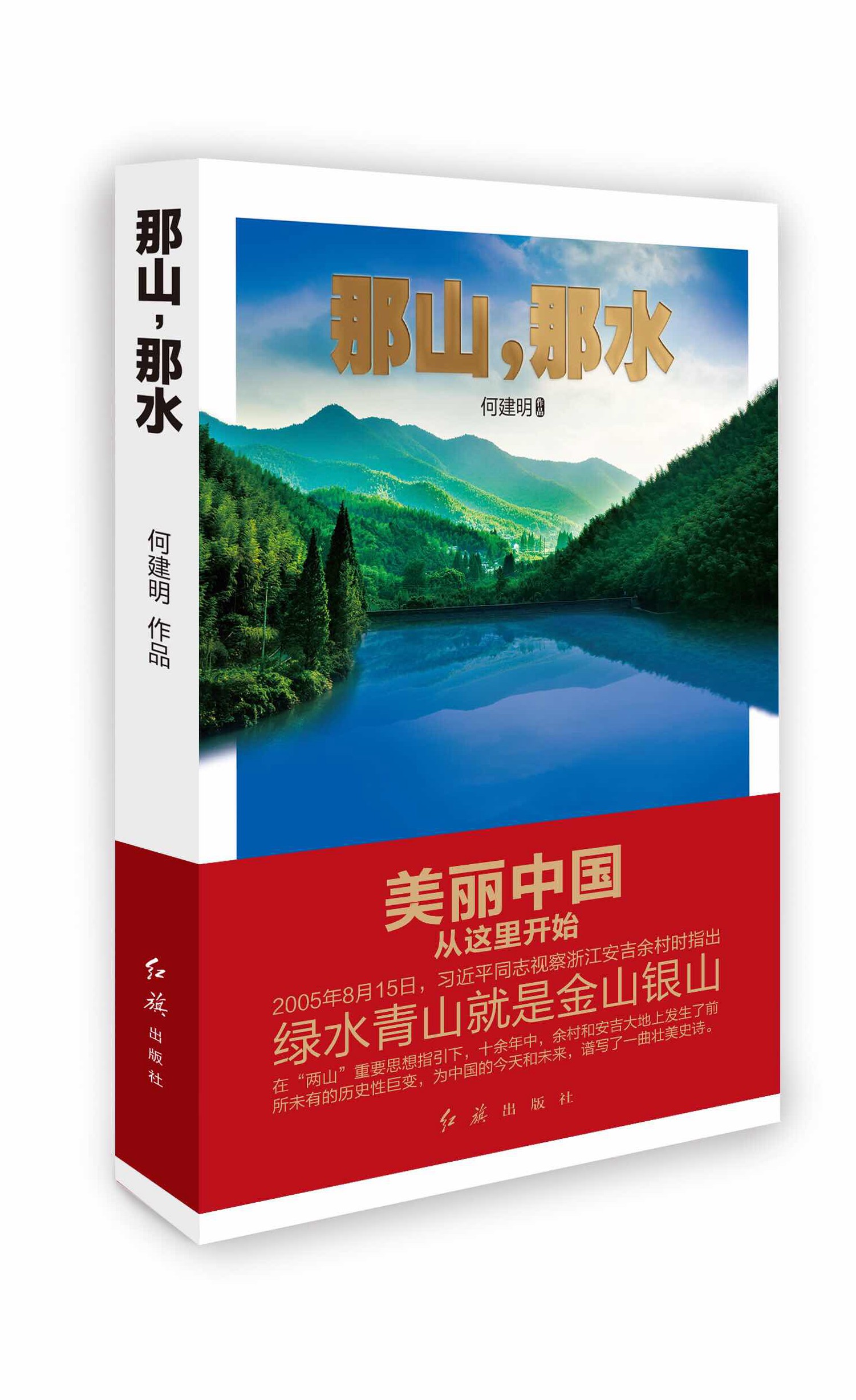《那山那水》 陆 『当代陶渊明』史话
2017年10月23日 16:03 《那山那水》 何建明
“葡萄园才是。”俞金宝说到葡萄,就像说到他在南京上大学的女儿,立即喜形于色。
“我的葡萄跟人家不一样,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卖,十块钱一斤,我从不拿出去卖的,是客人到我葡萄园里采摘后按斤算钱的……”俞金宝很得意这一点,关键是“我的葡萄比城里和路边上卖得要贵,一般都在三十块钱左右一斤,而且供不应求。”
“为什么?越贵越有人要?”我有些不解。
俞金宝憨笑中有几分狡黠,“不是,是我的葡萄生态。”
“怎么说?”
“我的葡萄园里从不喷洒任何农药和添加剂,一般的葡萄种植都做不到,可我做到了,而且一直坚持下来,所以葡萄的口感和含糖量绝对与众不同。”原来如此,长着一对虎牙的俞金宝真不一般哩!
“可据我所知,凡是农作物,免不了有虫啊蝶啊的,你怎除掉这些危害葡萄的‘坏蛋’呢?”我的问题虽然有些幼稚,却是农民无法回避用农药的关键所在。
“你跟我来。”俞金宝说到这里,领我走进了几十米远的葡萄园。
四月的葡萄园,新苗还不茂盛,不够壮观,这使廊架间显得有些空荡。俞金宝走到葡萄架中间,一边掐着葡萄嫩头,一边对我说:“种庄稼少不了虫啊草啊,一般都靠农药或锄头来解决,但那样结出的果实里肯定会残留些药物,对人体多少有些危害,可不打农药,不施一些添加剂,像果树这类东西产量又不高,怎么办?尤其是像葡萄这些蛮娇气的植物,你还得经常松土除草,地里的营养不能被茂盛的杂草抢了去,但葡萄园里又是棚棚架架的,人在里面活动多了,有可能会撞坏果实……”
可不,还是不小的难题呢!
“你怎么解决的?”我好奇地问。
“我在葡萄园里养鸡、养鸭,让它们吃虫子、吃草……”俞金宝说这话时一脸憨笑,“结果虫子除了,草除了,鸡鸭长大了,还能生蛋,可以给客人供应味道不一样的土鸡、咸鸭蛋什么的。它们的粪便又都留在田园里,成了葡萄的肥料,这不是一举三得嘛!”
原来如此!“俞金宝啊俞金宝,你太厉害了!你不发财谁发财嘛!”我听后,不由连连瞪眼惊叹。这个余村人太不简单,别看他一脸憨相,其实很精明。
“也不是什么精明。当年听了习总书记留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后,我就想,我是一个农民,怎么才能把环境和生活变成好生态的呢?农民种地,过去只是想着把粮食种出来,没人去想种的东西、吃的东西生态不生态,或者说生态不生态跟我没关系。可后来不一样了,我们余村曾经靠开山挖矿挣钱过日子,后来矿关了山封了,靠什么过日子?我们农民不能把绿水青山喊成一句口号,还得把它变成实实在在的能填满肚皮、能给儿子盖房子、给女儿做嫁妆、过上好日子的真金白银啊!是不是?”
俞金宝其实很能说,尤其说他自己的事,滔滔不绝。
“在村里的企业关停后,开始几年我自己也办过厂,在外地跟着人家学。后来听说村里的胡加兴搞漂流,人气旺得很,就有点眼红。于是就回到村里,也想着搞点既生态又赚钱的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我们这些农民眼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地里、家里变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有滋有味,能让城里人到你这儿来吃喝玩乐,再开心地住上几天;就是人家一批一批地走了,又一批一批地来了,你自己一口袋一口袋装钱的光景……不知我这样的比喻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农民的话很朴素,但道理深刻。俞金宝用自己的实践和行动,抓住了“两山”重要思想的根本。
“我感觉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个生态问题,就是让不好的生态变成好的能够变金子换银子的好生态。”俞金宝说,“照着这个理解,我先把竹林管理好,让它一年比一年茂盛,跟村里的大竹山环境融为一体,让整个农场的空气新鲜、清纯;再利用竹林的优势,开辟一些游玩的小项目;再把茶园建设好,保证有较好的固定收入。在这两个基础上,我开了农家乐,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后,我又开发了葡萄园。采摘的人一批又一批地来了,回城的时候总要带个十斤八斤回去,这样我的葡萄不用到市场就已经卖完了……现在每年供不应求,利也不薄。”
这就是俞金宝的聚金蓄银之道。
“其实就是两个字—生态。我赚的都是生态钱!”在余村,在安吉,像俞金宝这样的农民,依靠生态赚生态钱的人很多,甚至可以说,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讲生态、行生态,将自己的生存与生活融于生态环境、生态学问之中的人和事,比比皆是,蔚然成风。
我探访余村的日子里,走了安吉的一些地方,结识了许多令人敬佩的“安吉生态人”。任卫中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安吉可谓大名鼎鼎。
也许除了上海和安吉之外的人并不知道,“安且吉兮”之地还有一块金字招牌—“黄浦江源”。
我们对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黄浦江都太熟悉了,但连我这样的“半个上海人”(我母亲的娘家和我的娘舅都在上海),对它的发源地也是不清楚的。是太湖,还是其他?初到上海的人,必到黄浦江,因为那里是上海最美和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上海因为黄浦江才具备了“海派”的妖艳与风情,因为黄浦江才有了激荡的历史声浪与文化内容。
小时候,没有想过黄浦江源头的问题,只知道上海有黄浦江、有外滩才那么美。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能把谈恋爱的对象牵到黄浦江边的外滩并借着若明若暗的街头灯光,听着江上轮船汽笛声声,倾诉心中的那份羞涩,总觉得是最美最惬意也最过瘾的事,常流连忘返,心醉人不归。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去享受黄浦江给予不夜城的那种风情与浪漫,而不曾有人想过黄浦江的“母亲”是什么样,在何处。
现在的上海人,包括我这样的半个上海人都知道了,黄浦江源头在浙江北部的安吉。是谁想起了“黄浦江的母亲”?又是谁找到了“黄浦江的母亲”?上面提到的任卫中,就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

浦江之源 沈伟明 摄
我称任卫中是“现代的陶渊明”,或者说是个当代生态理想主义者。
那天,我被安吉当地人带到一个叫“剑山”的村庄,进了一个院子。那院子里有五栋楼,仔细一看,全是木结构和土制墙的房子。院子中央是一片菜地,那蔬菜都被一个个一米见方的“盒子”框着—别开生面的院子。
这时,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过来与我们握手。他说他就是任卫中—安吉民间生态第一人。他自我介绍后引我进了他居住的“正房”……
一栋内有小天井的土楼,上下三层。“你看,我这房子没有用一根钢筋,全部都是土木结构。桌椅板凳、日常用品,也都是就地取材,还有我们农家养的植物。”皮肤黝黑、浑身上下沾着泥土的任卫中似乎不像一个知识分子,倒像一个道道地地的庄稼人。他太太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但也是一副农妇模样,默默在一旁为我们倒水沏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