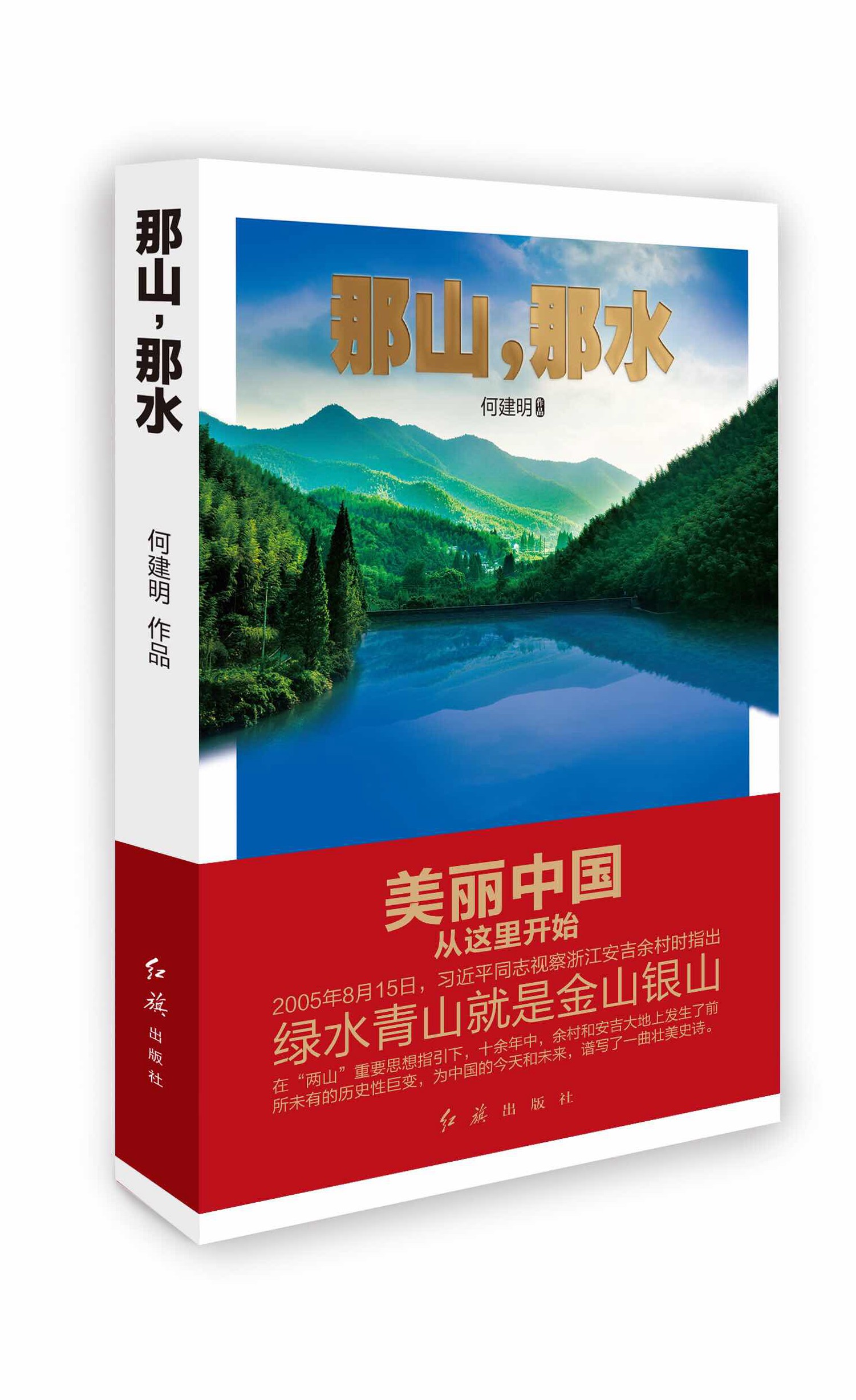《那山那水》 陆 『当代陶渊明』史话
2017年10月23日 16:03 《那山那水》 何建明
陆
『当代陶渊明』史话

青山绿水中的度假村 金国华 摄
到余村采访的第二天,我同随访的村干部步至村尾,远处二三百米处田间的一幢农舍和一片塑料薄膜搭起的菜棚,格外醒目地跃入眼帘。
“这是金宝农场,主人是余村的‘生态公民’,我们俞氏本家俞金宝,他家的农场……”村干部俞小平一边说一边直奔而去。
“慢点慢点,刚才你说他是 ‘生态公民’?”我突然止步,拉住俞小平,想澄清一件事。
“是。‘生态公民’是前年一群‘老外’到他家给他起的名。”俞小平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在余村,‘生态公民’比过去农业学大寨时的五好社员还吃香!”
“生态公民”,听词意很容易理解,但到底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算是“生态公民”呢?令人很想探究一番。
“这就是‘生态公民’俞金宝。”进了农场大门,俞小平指着迎面而来的一位身着灰色衣服的中年男子,介绍道。
“果不其然,满身生态!”我打趣地跟浑身上下都是泥巴的农场主人边握手边开了个玩笑。
“不好意思,今天有两个葡萄棚要搭起来,身上弄得全是泥……”长着一对虎牙的俞金宝满脸羞赧地搓着手,一看便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
“这四周都是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菜地,就你一户居于田园之中,此乃真正的田园生活啊!”我看了看俞金宝的农场内置,原来是几间草叠土搭的房屋,很原始,也极生态,不由触景生情地哼了句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次
其五》)没想到,话音刚落,一间小木屋里立即飘出一串清脆之声:“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陆游《游山西村》)呵,谁在吟诗啊!
“我的客人,杭州来的大学生。”俞金宝忙说。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嗨,这是一个小女子的声音。
“你这里莫不是田园诗地!”听着朗朗吟诗声,我忍不住惊叹起来。
俞金宝有些不好意思:“我没念几年书,听不太懂他们的叽里咕噜。住我这儿的城里人,都喜欢在这里一边看着风景,一边摘着葡萄,一边嘴里念念叨叨的。时间长了,两天听不到这吟诗声,心里就有些发慌,怀疑自己哪里服务不周了……”
我笑了。俞金宝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虽没有多少文化,但心像秤砣一样实在。
年轻时,俞金宝也是余村石矿上的一名苦力,开运石的拖拉机。“一吨载重的车子,我们常常要装八九吨!石头装过头顶好几尺,不开动车子都看着心悚,一发动,车子摇摇晃晃地在山道跑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上的石头就会砸到你的后背和后脑勺上……”到矿上干活时,俞金宝刚满二十三岁,明知干这运石的活危险得要命,但为了一天能多挣一两块钱,他也干起了这“棺材边爬进爬出的活”。
“没办法。那个时候,为了挣钱,就是不要命。”俞金宝说,跟他一起到矿上干活的另一名拖拉机手,就是在运石途中被石头压死了,一起死的还有一名帮手。
“后来我到了水泥厂工作。厂里干活虽说没有在矿上运石危险,但也不是人待的地方。”俞金宝说,“那更是短命的地方!”
“嗯?”我不懂。
“污染太严重。一天干下来,鼻孔里能倒出几两灰……我们村里许多人因此得了肺病,或者落下残疾,或者不到四五十岁就去见阎王了。”俞金宝想起往事,连连摇头、叹气。
“所以,后来村里关掉石矿、搬走水泥厂,我举双手赞成。”俞金宝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但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也能倒出一盆闪闪发光的珠子来。
“开始村里人确实很担心,因为我们余村过去是靠开矿办厂致富的,比起邻村,我们最差的人家也要算富的了!但,一关矿,一搬厂后,大家收入一下子低了很多。一时间,不知道前面的路往哪儿走。”俞金宝说,“后来村里向我们传达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习近平的话,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是农民,不懂太深的道理,可习总书记这句话我们懂啊,就是说,过去我们开矿办厂虽然能发财,但那样把山破坏了,环境搞坏了,人得毛病死掉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那种日子,即使口袋里装满了金子银子也没有用!习书记的话就是说,像我们余村这样的山村,如果山重新长绿了,水重新变清了,城里人就会来游玩,他们来了,我们就有了金子银子,生活就会更好……当时,我就是这样理解习书记的话的,这些年也是照着这个话做的,一直做到今天。”
“听说这儿连‘老外’都喜欢上了!”
“是。杭州开G20峰会时,一批‘老外’来我这里,都是欧洲人。听他们自己讲,以前一提中国的乡村,印象中都是些又穷又脏又落后的地方。哪想到他们一来就被我们村里的好山好水迷住了,而且都说在我这儿玩得开心、吃得放心,还夸我是‘中国生态农民第一人’!他们来了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很快就把我这里的一景一物传到他们的朋友圈和国家去了,我一下子出了名!后来就有‘老外’接二连三地来。看着我的生意好,村里的人非常羡慕,说我命里注定福气好,因为我的名字里就有金银财宝……”老实巴交的俞金宝其实还有幽默的一面,他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俞金宝的农场正房,是个“井”字形的中式庭院,看上去很土。“‘老外’喜欢这个样儿!”俞金宝一笑就露出一对虎牙,显得格外憨厚。就在我直想摇头时,他拉开侧屋的后门,引我踏进他的“暖房”。这下惊呆的是我—此处真是别有洞天。塑料暖棚下,有古趣横生的小桥流水,有鲜花盛开的花圃,还有参天高昂的松柏,有露珠滴翠的青竹,以及茶座、居室、观景亭……和与之连成一片的葡萄园、蔬菜园、茶园、竹林,甚至还有一条两岸盛开着油菜花的清澈河道。
“原来金宝农场的宝贝全在这儿哪!”凡第一次观光者无不为眼前的这番景象所感染、惊喜。
“在我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生态的。吃的、用的,基本上都是我自产、自种和自养的……”俞金宝自信地说,“来我这里吃喝玩乐一切尽可放心,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机和纯天然的,而且保证所有庄稼地里采摘来的、河里抓来的、棚圈里揪来的,都不会沾半点农药,绝对生态!”
“名不虚传的‘俞生态’呵!”我抓过放在桌上的煮笋,边吃边夸赞这四季如春的生态房。
“除了地里种的、圈里养的,其他你们看到的,都是我女儿设计的。”俞金宝骄傲地告诉我,女儿在南京上大学,学的是园林设计。
“我说嘛,外行谁能设计得这么有品位,这么专业!”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俞金宝的生态农场最出彩之处,是让他远近闻名并且大把赚钱的“金三宝”。
“金宝,你快亮亮家底!”村干部俞小平扯了扯俞金宝的袖子,农场主竟然满脸羞涩地喃喃道:“就是地里的这点白茶树、葡萄园,还有山上那些毛竹……”他指了指青山上绿油油的竹海。
白茶、葡萄、毛竹,这三样东西确实是俞金宝的“三宝”,因为它们是这位余村人致富和成名的金贵之物。青山上的毛竹,不仅可以满足俞金宝一家最基本的收入,还可以保证他开设的农家乐饭店长年有吃不完的鲜笋及竹园里养殖的活鸡等家禽和菌类,更主要的是能够让远方来的洋客人和城里人一年四季到余村来都有处可玩,有景可赏。这不是宝还能是什么?第二个宝是白茶树。白茶树是余村和安吉人除毛竹之外最重要的宝,俞金宝自然知道这一点,自己的白茶园就是一个小银行,但这都不是俞金宝的得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