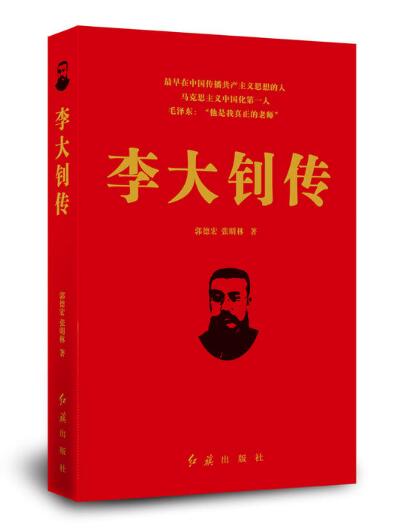《李大钊传》
2016年12月26日 15:26 红旗出版社 郭德宏
伯夷兄弟劝阻武王无效,虽然回到武王之父文王下令所设的“养老院”,但武王伐纣当中血流漂杵的暴烈举动,越来越使这两位老人不能再容忍。从而,最后的悲剧终于发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他们直到饿得将死的时候,仍然作歌明志,不改其观念主张。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兄弟俩就这样,“遂饿死于首阳山”。真是太惨了!
伯夷、叔齐的事迹、意义,凡是接受科举教育的人,是没有不熟悉的。对于这两位以死殉名的人, 《论语》提到有4次, 《孟子》提到有10次, 《尚书》提到有2次。孔子与孟子,都称他们是“古之贤人”。孔子称他们在大权威、大一统面前,也敢“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称他们虽“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而“有马千驷” 的权贵齐景公,“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大权威,其实也都是一种可怜虫!而伯夷、叔齐,则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并称他们是:“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等等。所以,凡是苦读《四书》、《五经》的学子们,肯定对伯夷、叔齐的事迹,都有感于心。但是,书本上的了解和处于历史遗迹和一定的文化氛围当中的感受与领悟,却终究是很不一样的。
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早已注明:“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当代史家,对此又作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孤竹国都城约在卢龙县城南或城西南某地。“孤竹” 二字,在甲骨文、金文中,也已出现。这个小诸侯国, “国君和辅佐国君的少数人来自中原,而其辖区内的多数居民为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著民族”。它的范围“不限于都城及其邻近地区,至少包括今卢龙、昌黎、抚宁等县境域”。
在卢龙县城及其附近,当时古文化气氛是比较浓厚的。在城外有相传的首阳山,也就是夷齐饿死之处,供人们在这里凭吊。另外,远处还有书院山(原属昌黎),山的石屏下,在一洞井之旁,石壁上镌着“夷齐读书处”。这也使后人肃然起敬,并起着立身劝学的作用。这些对善于感应历史社会和文化气氛的李大钊,也都是生动的具有感染力的教材。到了这里,他对于孔子所赞夷齐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等语,自然地更会有一番新的体悟。
1913年秋,李大钊赴日留学之前曾游碣石山,在游记中说:“倦游归去,长歌采薇,悄然有慕古之思矣。” 伯夷叔齐临死之前所作的歌,历来被称作《采薇》歌。“长歌采薇”,也就是与同游人一起高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这里所谓“慕古之思”,也就是慕伯夷叔齐的高风亮节。由此也可见,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所受的历史遗迹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