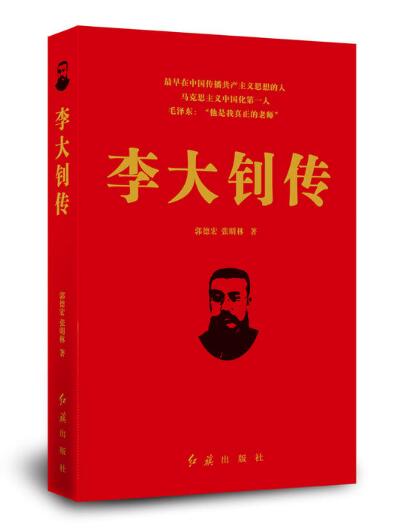《李大钊传》
2016年12月26日 15:26 红旗出版社 郭德宏
赵先生此时在离大黑坨村1公里远的小黑坨村张家专馆教书。他曾是昌黎县学的“增广生”,学问、名气都在单先生之上。但两年之后,出于更高的要求,李如珍为孙子换了第三位老师。这位老师是在距大黑坨村10多公里的乐亭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家教书的黄宝林先生。宋举人曾在山东任过候补知县,黄先生则是曾到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名气、学识又较赵先生为高。有了先前祖父的启蒙,特别是在祖父督促下养成的刻苦努力习惯,耆年在私塾进步很快,成绩优异。这为他增加了自信心。
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以前,学校的基本职责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科考内容大体是固定的,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乃至乡间私塾的教学也大体围绕这些内容。
乾隆年间规定的,一直沿用到清末学制改革前的地方官学所用教材为“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等。
其中“四子书”即“四书”,是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在此期间历届的科举考试几乎都从“四书” 的范围出题,所有科举考生都要把“四书” 背得滚瓜烂熟。那些落第的文人再去设塾教书,也还是要让弟子学习这一套知识。单子鳌、赵辉斗、黄宝林几位先生当然不例外。
“四书”内容丰富,体现了儒家对人生道德伦理的看法和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原则。如《大学》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学做圣贤的道理,就是使人内心中本有的光明道德得以显现出来,每日更新进取,达于至善之境。要做到这一步,需要从最基本的“格物”,即充分研究了解宇宙世间万事万物之“理”开始。“格物”目的是达到对万事万物的“知”;有了充分的“知”,就会有一心向善而不自欺的“诚意”;由此端正内心,不被愤怒、恐瞑、狂喜、忧患牵制;做到心有爱戴、厌恶、敬畏、怜悯、鄙视之时不致偏颇,“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达到最好的修养境界;由此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使子弟知孝悌慈仁;由此可以为邦国作表率,以絮矩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忠恕之道、仁义之德治理国家天下。
《中庸》讲天、性、道、教的统一;讲喜怒哀乐都有节制,符合一定场合个人身份角色应有的合宜要求;以此“中” 为人之言行准则,众人之“中和” 为人群社会理想之状态。譬如舜有大智,在于他好问好思索身旁人说的话,不好的不管它,好的就接受发扬,把各种意见的两极观点折中,用于指导民众。
以当时人的知识,理解四书的语言,应当和我们今天用白话译过的原文一样容易明白表面之意,但系统深入的理解,尤其是联系国家社会为政道德心性之类的内容,不要说对一个孩子,就是对一个一般的乡间塾师也未见得说得透彻明白。
但是,处在求知欲望极强烈而记忆力极好的年龄,为了应考而必须背诵原文和“破讲” 重要段落的意思,甚至还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其他经典和史籍的学习,边扩充知识,边加深对儒家思想精义的理解,这便使儒家经书中的若干思想内容给少年时期的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对于他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