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雷不鸣 | 如果我们素不相识
2017年04月25日 17:00 旗书网 聂磊旻

我写这篇文章时,绿皮火车正冲出雾色苍茫,冲出绝域德令哈——就是海子诗里的那座绝情小城德令哈。
这似乎是一种宿命。
3年前,诸位在这个公号看到我的第一篇文章,写得正是德令哈。
那是2014年的夏天,采访完巴西世界杯,我单车万里奔赴德令哈参加海子诗歌节。回来后,老东家请我喝酒洗尘。闲聊中,说要不在这里写点东西。那时我刚好经过一个月写了十万字的血战,每周写一篇,简直就是让西门庆情挑潘金莲。一拍即合。
3年过去了,我发生了些许小事,好在大势不改,吊儿郎当、酒来碗干的心性还在。
我难受得只有一件事:太多人离开了。

最早负责这个公号,催我稿子催到披肝沥胆境界的编辑小思,已经离职两年。在她离开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一种“暴雨将至无处躲藏”的文字不安。
之后文艺青年八圈接管,他采用无为而治,顺我自然。写了大半年,他给我弄了两条市面上很难买到的“牡丹333”,说拿走抽就是。我这才知道他是个有心人,可他在去年也离职了。
之后又换了两个编辑,时至今日,负责约稿的是一个95后的小姑娘,比我还不靠谱,经常一个月无影无踪。倒是我经常在微信里吼她:“你到底来不来催稿的!你不催,我怎么写得出啊?”
这些年,不少姑娘绝情远去,不少兄弟摔杯离座,倒是最无长性的我还在,很是荒谬——看着德令哈的夜色四起,我不断地想,“如果我们素不相识该多好”。
其实左读这个号和人很是好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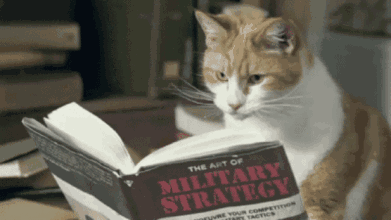
它隶属于红旗出版社,编辑们每天校书、改书、排版……根本没有太多时间运营它。人家做商业公号,越做越兴旺,红旗的编辑们倒好,弄得像在四川卧龙保护中心工作。为啥?因为粉丝少得像大熊猫,全属于国家濒危保护动物,必须细心呵护。
2个月前,我请编辑们喝酒,我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号有多少粉啊?总编辑写的文章居然才几百点击率,换成是我,自己掏钱也得去买点粉。拍马屁会不会的啊?”
一个编辑很严肃地说:“粉是不买的,能关注的都是铁粉。”

我沉默了一会,说,那有没有作者给读者打赏的功能,我想给我的读者打个赏,这三年,他们太不容易了……
单论文字,这些年里,我早已敲出几百万,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我写的。
年轻的女歌手花粥唱:“一腔诗意喂了狗”。我感觉不错。

这些年除了一些评论专栏和深度报道,也就“左读”随我恣意选题,长短不限,一边坚持词穷和孤勇,一边坚持贵气和真情。
三年了,从未想到一个如此认真严谨的公号能允许我的文字存在这么久。
一个月前,红旗总编说,写了三年了,不容易,集结出本书吧,也算一个念想。
我说,好啊好啊,这样我家厕所就有纸了,书名我早就想好了,《小浪底》。以后出续集,直接《大浪底》。

车过德令哈,我正在餐车喝酒,列车员说,德令哈到了。一旁的小年轻们像我那年一样背起海子那首《车过德令哈》,“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谢谢大家在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
谢谢我们相识了这么久。
编后:
三年前,小聂开着刚买不久的小吉普,一个人千里行军奔袭到德令哈。三年后的4月24日,他再一次穿着大棉袄,抵达了刚下完春雪、气温零度的德令哈。前一天是世界读书日,海子被人热烈地惦记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腻翻N条大街……而我们的专栏博主小聂,从未婚到已婚,从体育记者到企业白领,从三十走向三十五,人生刷新到了一个黄金时间……唯有什么未曾改变?就是一腔海子式的浪子情怀。非常佩服小聂,坚持了三年多的公号写作,发表在我们这块冷门的卧龙岗,不嫌弃不放弃,只为倾诉。我以为他不会有长性,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我坚持了一年多的左读专栏写作,去年断流,今年春节过后复流,已物是人非。所以,才情,就像一头奶牛,挤一挤,总是有的。所以,任何理想主义,都带有伤感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