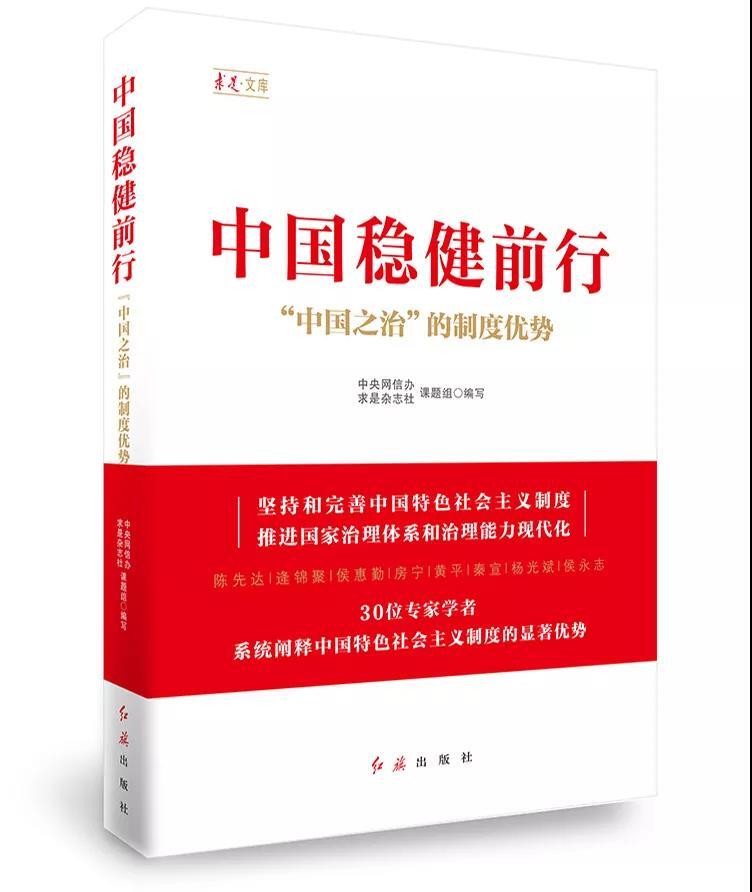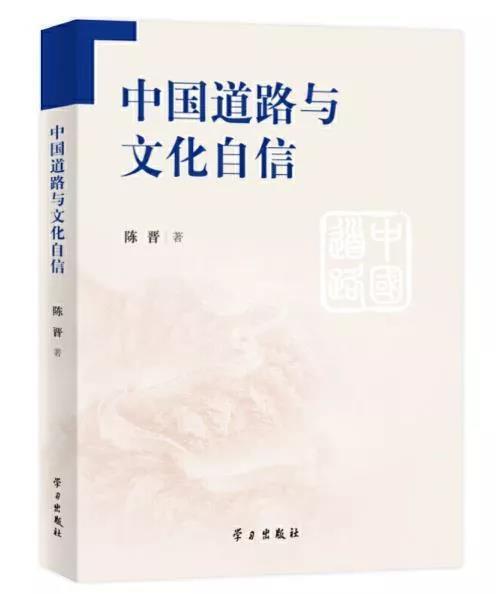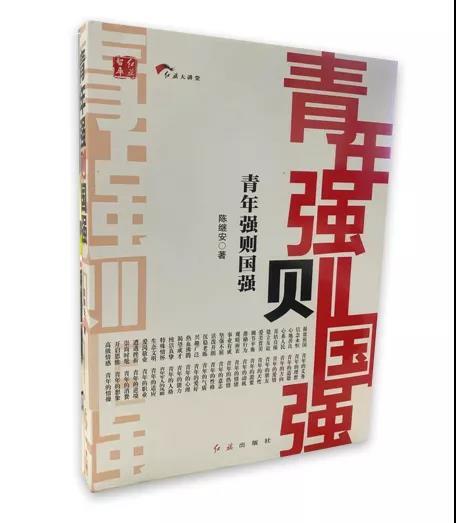《红镜头》书摘
2016年10月19日 11:41 红旗出版社 顾保孜(作者),杜修贤(摄影)
“咕咕……咕……”母亲饱含深情,手里握着一小把谷糠拌菜的鸡食,撒在地上。母鸡霍地跳出窝巢,俯首盯着母亲粗糙的指尖,不等糠菜落地便啄进了嘴里。
我爬下炕,光着脚丫子站在门槛里,看见母亲容光焕发,似如珍宝看着鸡群,心里也欢喜起来。“咚咚……”跑到母亲身边,紧贴着,希望从母亲腋下看一眼鸡娃,可母亲看也不看我就将我一把推开。她正在全神贯注地倒提每一只小鸡的脚,看鸡头是向上勾还是向下垂,以此来断定是公还是母。
我咧嘴大哭,母亲仍然不看我。嚎啕中,听见母亲念叨:“这是母鸡,这是公的。”
几天后,小鸡跟着母鸡开始在院子里溜达,“咯咯……”“叽叽……”伟大的“母爱”牵着十几个毛绒团在地上滚来滚去。我喜爱它们,渴望将这美妙的情景讲给常夸“我娃灵,我娃能说会道”的父亲听。记忆里的父亲有时面目模糊,细细想去,不知是大眼小眼还是长脸圆脸。一旦出现在眼前我又会深刻地记住父亲的面目。他离我们并不远,一出门拐几个弯就是他做事的地方。听母亲说,父亲在我们小小的米脂城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打得一手好算盘,祖上曾是个大户人家,不知在哪一脉蔫了香火,渐渐地败落了下来,到父亲这一辈除穷得只剩下认识几个字外,几乎一无所有。
兄弟们无法捆在一起,父亲排行老小,分房屋家产轮不到他的名下就光了。只好和母亲租破烂不堪却很便宜的土垒房住,生下了哥哥、姐姐和我。
父亲的算盘已系不住我们兄弟姐妹不断增长的嘴。哥哥姐姐五六岁就上街拾菜叶和瓜皮,充填家里煮饭锅里的容量。盐水煮菜叶,盐水煮瓜皮。我几乎记不起来白面馒头的模样,更不要说回味它的滋味了。
母亲也常出门,她做得一手好针线,常到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得来一点工钱,筹划全家人的油盐酱醋和针线布头。
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外面黄泥土被人踩得像碾过一样,没有草,没有树,一块一块凸出来的土地被磨得油亮油亮。我喜欢这坚硬的地面,至少它不会无缘无故地掀起黄尘迷住我的眼。我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小鸡们好像知道我的孤独,挨个地滚过我的光脚背,痒丝丝的。我开心地大笑,小鸡一惊飞快地逃向它们的“保护伞”下。我撒开脚去追。这下激怒了母鸡,它扇着翅膀,拉出干架的样子,尖嘴对着我的脚指头。我一跺脚,它却掉头就逃,丢下一地滚得乱七八糟的鸡娃。我开心极了,跟在后面追。
“叽——呀”,脚底一热,低头一看,“哇哇……”我惊慌地大哭了起来。
小鸡死在我的光脚板下,血溅在地上也溅在我的脚上。我吓得将脚底板在黄土地上搓一下挪一个地方,院子里留下了歪歪斜斜的血印子。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是母亲!我紧张地溜进屋里,靠着黑黝黝的灶台旁,希望母亲找不到我。
“咣当——”大门推开了,沉寂后是一声大叫:“谁把鸡娃子踩死了。三娃子,出来!”
我抑制不住恐惧大哭了起来。不等看清母亲气冲冲的表情,只觉得耳朵根子一阵剧痛。我被揪到小鸡死的地方,巴掌没头没脑落在我身上。剧痛中,我还拼命地叫唤。
倔犟的挣扎又换来一阵巴掌,而我却越叫越凶。
最后母亲气恼地推开我,任我又滚又哭地撒野。最后,我哭叫累了,迷迷糊糊在地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