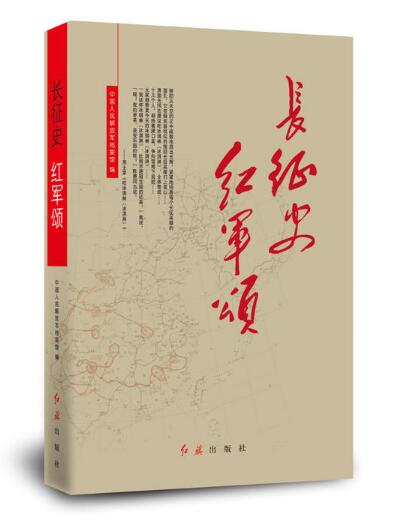《长征史 红军颂》书摘
2016年11月08日 16:55 红旗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
关于编辑的经过
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字林西报》曾有以下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大意如此,现无原文参考——笔者)这位帝国主义代言人虽然是在破例的惊叹红军的奇迹,但他也在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可是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在〔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苦的嘲弄。
编辑这本书的动机,是在去年的春天,当时的计划是预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写的人偏忙着无时间,一直延宕到八月。事实告诉我们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于是发出征文启事,并又从组织上和个人关系上去发动计划中必需的稿件。
征文启事发出后,我们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比拿枪杆还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铅花里的人们,是否能不使我们失望呢?没有人敢给有把握的确信。然而到了八月中旬,有望的氛围来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更是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兴奋,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到了十月底收到的稿子有二百件以上,以字数计,约五十余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我们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我们决定[采用]以下几个方针:
一、同一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
二、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
三、有些来稿,只是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
四、有些来稿虽然有独有的内容,但寥寥百数十字,而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
五、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
六、编次的方法,是按着〔照〕时间和空间。
此外关于统计等等,是依着命令、报告、各种日记和报纸汇集的。
我们把这约三十万言的稿子汇齐了,然而看一看目录,却使人有极大的不满,这里所有的还不到我们生活过的和应该写出的五分之二!然而我们不能再等了,环境和时间都不容许我们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这本书本应早日和读者见面,但因稿子大量涌来后,编辑委员会的人员出发了,结果只有一个脑力贫弱而又肢体不灵的人在工作,加以〔之〕原稿模糊,誊写困难,以致延长预定编齐的期〔时〕间约两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编者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