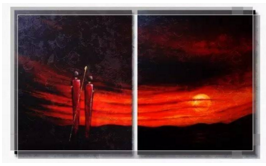试棺者孙仲旭
2016年07月14日 16:25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云也退
【上周五晚上,我跑完步回家,羽戈发我微信,说微博上在传译者孙仲旭去世,向我求证。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怎么可能。我拨打了孙仲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稚嫩的声音。孙仲旭的儿子跟我确认了这个事实。瞬间我就懵了。我不知道那个晚上他接了多少个来问询的电话,反而是他在电话中试图安慰我。
像拼图一样,事后我才从各种消息里慢慢还原前后。大概是他已经被抑郁症困扰多年,之前住院了一阵,有所恢复后又回家。最终为病情所困,自行选择了结。
孙仲旭翻译了很多书,作者云也退在文中有细述。只有无比热爱文学才会在短暂的时光里埋头翻译。我一直看着他在微博上贴译文的片段,贴他在非洲拍的照片,他一个个去吃麦当劳和肯德基并做评价,这似乎是他的爱好。还有他同儿子的许多对话,如今看来,令人唏嘘不已。
云也退说孙仲旭翻译奥威尔时大哭。我确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微博摘录了许许多多奥威尔的文字。幸得是他,我们更贴近了英美当代文学一些。
以之纪念。
感谢云也退授权左读转载。】
互联网的功绩之一,是让一个人的故事,他的爱、困惑与死亡激起波澜,而互联网的恶劣,则是让你看到绝大多数人对此毫不关心,甚至反应苛酷。没有互联网时,我们的世界就这么大,我们知足于有限的、看得见的反馈,而现在,多少怨怒恚恨皆缘于亲眼见到了虚无,而我们的奋斗是在与它作无望的互搏。
孙仲旭去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在豆瓣上的个人作品豆列。浸淫文字和书之人,应该是冲淡的,因为他投入多大的努力,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体现在别人眼里不过就是一块统一规格的封面,真有“广厦万间,卧眠七尺”的味道。我读过不少译本,译者在后记里谈“译事之艰”,例行公事地(在我看来是这样)感谢所有要感谢的人,妻儿老小、师友、责任编辑,等等,这些字都是给自己写的,自己在乎,但不敢妄企他人的在乎;甚至作者也是,多少次我看到卷首的“致中国读者”,心中便想:“中国读者”,这个人群有多大呢?其中又有多大的比例,会在乎这个“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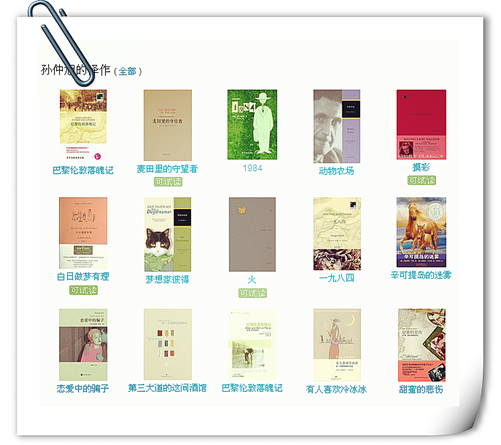
写字从来便是一桩枉抛心力的事,写字者最大的慰藉,甚至不是拿到高额酬劳——那已经不叫慰藉了——而是看到多少自己钦敬的前贤也长期苦于枵腹,忧于来日。看豆列,孙仲旭所译之前辈作者,我读过的很有限,但我知道西尔维亚•普拉思曾经四度自杀;雪莉•杰克逊英年早逝;雷蒙德•卡佛挣扎在赤贫线上;理查德•耶茨的抑郁很有名;乔治•奥威尔在年近不惑时仍在为生计恐慌,急于找份工作,最后好歹在BBC当上了战时播音员,可他又太认真,整日愤恨于战时媒体的满口谎言、扭曲事实,他写《一九八四》,部分灵感便来自在BBC所受洗脑的经历。
普拉思,奥威尔,杰克逊,耶茨,深受耶茨影响的卡佛,还有早早隐居的J.D.塞林格,甚至包括伍迪•艾伦,此外,还有孙仲旭虽未翻译,却影响了耶茨、卡佛等人的菲茨杰拉德。这些人,因为孙的缘故好像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和奥威尔一样,孙也是个太过认真的人,他不只把作品仅仅当作作品,当作一具标本,一个“他人的故事”;他每译一本,便要没入作者的内心一遭,衣其衣冠其冠,从头进去,从脚出来。他不只是译者,他还是一个试棺者。

他译奥威尔和塞林格时,我便问他为何去做一些炒冷饭的事。在我看来,普通读者如我,岂能放弃董乐山、施咸荣译本,来选读你的译本呢?董、施皆有大师才子之名,纵你有强过他们的地方,如不做一些宵小之事,例如断章取义地腆着脸吆喝自己,想有所“成”,可能性太小。孙仲旭说,他就是喜欢。喜欢,再加上编辑的邀约,这事就做了。
我知道他有多爱奥威尔,这位享寿不足五秩、病恹恹、阴沉沉的作家却是他翻译的起点,每重印一次,他就修订一番。过去不在意,因为他不是我的菜,但当得知,孙仲旭译《一九八四》译到嚎啕大哭时,我想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奥威尔了。
这不仅是出于对孙仲旭品位和人格的信任。读文学的人,尤其是读耶茨、读普拉思、读卡佛的人,都懂得只要有一个人痛哭失声,这世界——原谅我讲这么文艺的话——便值得推倒重来。
很多老前辈和不太老的前辈都说,做翻译,或者做广义上的文字创作,得尽量有份工作。命运待孙仲旭已相当不错,刚认识时,他便与我说,像他这样,没学过法律却能从事法务,领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还能有大把余暇做自己爱做之事,很好了。但说话时,我并不知道他会连年累月地翻译,至今出版了37本书。37,几近追上了他的卒岁,若他假自己以年,“等身”不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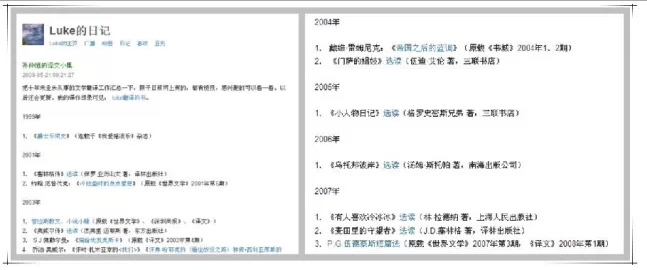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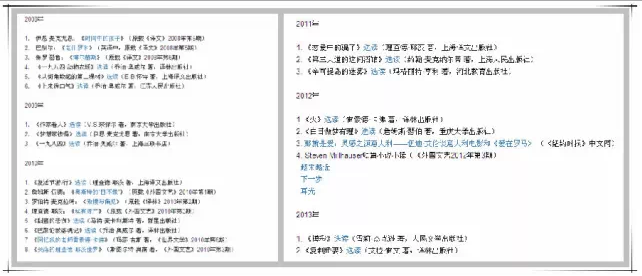
而现在我们知道,即便是如此的命运也不能削平这个平和的人内里的崎岖;甚或正是这种命运,才让他无法忍受继续这样下去,去面对又一个黑夜过后的白昼。我猜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分裂,以文学翻译为生之酷爱,却还得蹭蹬俗世聊以哺给,无法倾身于酷爱之中,犹如海因里希•冯•奥夫特尔丁根无法觅获那朵梦中的蓝花。就是这分裂,在那些不懂、不读、不屑文学的人,自然也不会去“凝视深渊”的人看来,难道不值得他烧一柱高香,额手称幸么?
以前读普拉思自传小说《钟形罩》,很疑虑为什么人们要赞赏那么沉重的书,一个女诗人亲身记录自己的毁灭,以女性少有的滑稽戏谑起笔,一步步进入常见的可怕的抑郁心境,时间越过越快,因为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寡淡、乏味、陈陈相因,再无新人可期,再无鲜美的云在月上飞扬。我想,或许这跟看恐怖片的原理是一样的:见到了别人的苦,合上书本后,才能享受自己的宁静。
但,一本文学书真的只是恐怖片么?编辑们都说,每次有英语新书都想着问问Luke,他们其实也都明白,这一本本的小说,而且大多是描写人的某种失败的小说,会磨损一个译者,不只是他的光阴,还有对生的理解和认知。最好的故事都是悲剧,主人公无可挽回地毁于他的人性弱点:他们建房子,他们铺路,他们相爱,然后,作者飞到空中或跳到对岸,高喊着“完了,完了,都完了”。我们掩卷,怅然仰首:是啊,怎么就都完了呢?
试棺者孙仲旭,多少次浸入悲剧又厮搏而出,以至于他的非洲之行,看起来都像是面对虚无最后的挣扎,让时间过得慢一点,甚至重焕新鲜。但是,还是让我们不建房子也不铺路吧;我们建一座房子在心里,铺一条路缠卷起来在灵魂里。我们在内部都会不死。在内部,一位杰出的译者能得到他想要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