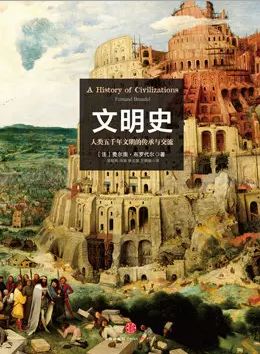关于布罗代尔《文明史》与伯樵书——“书中信”第二笺
2016年07月14日 17:05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公羊猫男爵大白
【公羊猫男爵大白先生又以写信为名吹捧了一下布罗代尔。之前我们转发过大白先生以书信体向李斯佩克朵致敬的文章,颇受好评(大雾)。大白先生以金融行业高帅富之身,以一轻巧之姿通文史两端,希望他能稳定地为我们供稿啊!!!】
伯樵伯爵鉴:
这是我第一次提笔给兄写信,离上次你我单独喝酒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次在我单位附近的“珍巷福地四合院”,饭菜委实一般,但我们聊了生活、电影、女人和学术圈八卦。不知兄是否还记得,我当时说起正在读的布罗代尔的《文明史》,你说“布罗代尔肯定牛逼”。再后来,我在豆瓣邮件里又问过兄对年鉴学派的看法,而此时此刻,我想再来和兄聊聊这本《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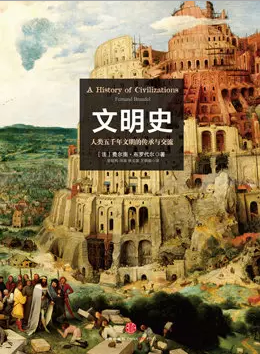
我要坦言,我没有读过布罗代尔最著名的《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在通读《文明史》之前,我只读过他的一本小册子《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杨起译),后者是他另一部巨著《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要点讲稿。但讲稿问世在先,原著出版于后,所以也勉强算是他认可的著作。
反讽的是,在我读布罗代尔之前,我对年鉴学派的认识虽然只是道听途说,却并不惮于和师友说起这个名词;在读完《文明史》后,我却对此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你肯定知道,这很正常,在学术领域,越是不了解的事物,我们越是敢于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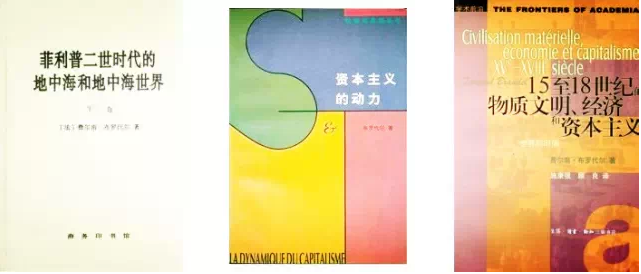
《文明史》你读过吗?如果没有,我先简单和你说说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在第一章,他先对“文明”这个词做了“集注”,把这个词诞生以来几百年里内涵与外延的演变悉数列出,这本身就像一个“长时段”的例证。而综合前三章,他则对研究“文明”提出了他一贯主张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通过“长时段”来研究“总体史”。这三章构成了《文明史》的纲要,大约占了全书15%的篇幅,在这里,他虽然提出了研究方法,但并未申明是研究一个文明的总体史,还是全部人类的文明史。
此后,他与汤因比细分各种文明的做法迥异,将文明分成非欧洲和欧洲两大部份,非欧洲文明包括了伊斯兰教世界、非洲和远东;欧洲诸文明还包括了美洲和俄国。他区分欧洲和非欧洲,显然表现了他对欧洲特质的极端重视,这与汤因比“不分大小文明一律平等”的政治正确不同,和斯宾格勒唱衰欧洲的态度也相反。事实上,布罗代尔有着可爱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这部书我读了很久,上次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说,他写得实在太精彩啦!你可一定要读,因为这是布罗代尔最后一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他可不像其他的法国学者,因为不会说人话,所以才搞出一套套的理论和框架。布罗代尔的叙事才能实在是太强大,他并不排斥对提到的每一件具体事实纤芥毕现的描摹,他的人话讲得相当好。
但是,他毕竟选择了和事件史背道而驰的史学方法。细思全书,我必须让自己摆脱那些精彩叙事的羁绊,努力试图理解他的意图。
他写这本书的直接动机虽然是为了介入彼时法国的中学教育改革,但我相信他肯定早有这样的打算,所以积累了许多材料才选择动笔。而且,我觉得,“文明”简直太适合用来做“长时段”和“总体史”的研究对象了。
但你我都知道,大师写下的东西并非都是高妙的,他们也会写出大受欢迎的失败之作。我吃不准他用他研究地中海屡试不爽的“长时段”和“总体史”的方法,来研究差异极大的各种文明,动机是否可行?结果是否成功?特别是当我得知《文明史》在布罗代尔死后出的单行本标题竟然是《文明的语法》(Grammaire de civilisations)后,我更觉得有必要仔细辨析这本书是否讲清楚了一个文明在结构意义上的“语法”(尽管这个题目应该不是布罗代尔取的)。所以,我很希望——借助你的看法——帮助我判断,这本书是否贯彻了他一以贯之的法则?
那么就像我们喝酒,我先干为敬。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横向看,布罗代尔从地理、社会、经济和集体心态这几个年鉴学派标志性的角度来对一个文明进行“四面出击”,这是“总体史”的写法;纵向,则是将上述分析置于以世纪计的“长时段”里。这样,试图让一个文明在字里行间自然显示出其特定的“语法”。
布罗代尔写道:“一个文明通常不肯接受那种质疑它自身的任一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这样的拒斥态度,或者说不言自明的敌意,相对而言很罕见,但它们总是指向一个文明的心脏……正如一个文明可以欢迎或排斥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分一样,它也可以接纳或拒绝它自己历史的残余物。这一选择过程并不缓慢,而几乎总是无意识地或部分地进行。但多亏这样,一个文明通过分割出其固有过去的一部分,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p64)。”
一个文明,短期看都是“稳定”的,长期看则是不排斥“变化”的,“如何稳定”(what)和“怎样变化”(how),就构成了一个文明的语法。布罗代尔所说的“文明”,是单一的文明,而不是人类整体而言的文明。
但这个语法如何表述?
我前几天特地读了台湾学者赖建诚的《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他就质疑说:“布罗代尔没清晰地教导读者说:看吧,我这样用长时段的观念,就可以从回教、中国、俄国史的素材,观察到从前所未理解到的历史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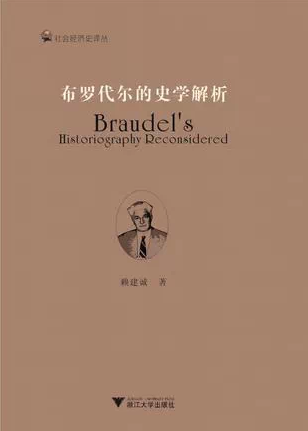
但是,我觉得,赖建诚的思路有问题,他不能像读一般的历史著作比如汤因比那样,去寻找某个文明清晰而又概括的“结论”,布罗代尔的风格不正是“我写出来的就是你看到的”吗?一就是全部,全部就是一。
我觉得布罗代尔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历史学家不相信斯宾格勒或汤因比这样的热情过度的探索者。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图像、地图、精确的年表和证据。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文明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实例,而不应仅仅依赖任何文明理论。我们迄今所概括出来的所有规则和解释,都将通过事例得到阐明和简化(P69)。”
所以,汤因比是谢灵运的玄言诗,每一首诗最后都带着条玄言的尾巴;布罗代尔是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把东西一列,看似没有语法,实则境界全出。
或者说,布罗代尔还像范宽画山水画,先在山里住上许多天,把峭壁丘壑溪水山林都记在心里,最后呈现在同一张画上。今人说这是“散点透视”,我觉得是瞎扯,这根本无关“透视”这种“单一理论”,套用布罗代尔来说,是一种“总体画”。你觉得我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吗?
总之,我觉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的史学法则和事例基本是自洽的。
但是,我仍然有另外的感觉。我读完《文明史》已经几个月了,正像恋人激情过后,留下的总是平淡、琐碎和疑惑,但也有对如胶似漆时的丝丝回味。
我回味《文明史》,却发现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他前言编制的“如何研究文明”的宏大观念和“长时段”、“总体史”等他惯用的术语,而仍然是作者在书中随手拈来的“事件”和他堪称点睛之笔的评论。譬如,他解释伊斯兰文明何以迅速崛起?并没有从什么政治、经济、军事角度进行平庸的探讨,而是举例证明伊斯兰教本身就是被中东和近东的历史所塑造的,穆斯林的一系列生活——向君主跪吻大地的礼仪来自古希腊时期的埃及;土耳其浴来自古罗马浴;穆斯林服装来自古巴比伦等。
因此他在繁复的例证后用一句话概括了结论:“恰如基督教承继了罗马帝国,是其延长部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近东……穆斯林文明把一系列古代地缘政治义务、城市范式、制度、习惯、仪式和由来已久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仰和生活(p76)。”这几乎是我见过对这一问题最令人信服的回答了。
因此,当我通读完全书后,我个人觉得,他真正写得丰满、有趣且足够体现他史学意图的,主要还是伊斯兰和欧洲文明。他是欧洲人,又在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呆过很久,所以这两个文明写得最好,最能体现出“长时段”和“总体史”的特点。但是其他的诸如远东、黑非洲,乃至美洲和俄国等,都写得过于单薄,特别是我们熟悉的东亚,他基本上只是引述西方汉学家的成见,没有体现出“总体史”的意图。
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在谈论每个文明的末尾以及60年代的附记中,总会多少写下一些对“未来”政治发展的预测。很可惜,正如蹩脚的国际关系专家对未来的预测一样,他的预测已经被历史证明几乎都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我们都知道,对未来越是切近的预测,越是容易落空,而对今后几十年内的变化进行预测,更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预测对了也说明不了什么。布罗代尔一代宗师,难道还不知道这个理儿?所以,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越出历史学的疆域?他是想把“长时段”一直延伸到未来吗?还是纯粹信笔至此根本停不下来?
我总觉得写这封信很困难。因为读布罗代尔很难聚焦到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只能和你谈论整体、谈论感觉,而我的感觉一向不敏锐。而且正像我承认的,他最重要的著作我没有读过。这种忐忑让我不得不求助于你。希望你谈谈你对他、对《文明史》、对我在信中提到的疑问的看法。
期待你的消息,下次喝酒,我建议去我单位附近的“洞庭楚乡”,那儿不贵又好吃,酒尤其便宜!就是人超级多要排号,你要提前来排号啊!
此致
秋安
弟:公羊猫男爵大白上
2014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