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完好的都已破碎
2016年07月07日 10:02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布克
【本文作者布克,女,媒体从业人员,爱书、爱咖啡、爱运动。家人知道,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读书就会发脾气。朋友夸性格好,不熟悉的人会认为有点怪。喜欢的生活:简单、明快、朝气。
感谢作者授权左读发布此文。】
看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缘于一位朋友的推荐。
那天我们在南山路上的西湖春天吃饭。我的朋友聊起了雷马克。他说,雷马克虽然不是一线作家,但他的书真很不错。他特别提到了雷马克的《流亡曲》。他说里面有个细节对他触动非常大。
他说,在那样的年代,满街都是吃不饱的人,他却想给心爱的姑娘买花。想想,这种情况下,一个男人走在街上,手里捧着鲜花是不是很奇怪,怎么办?他想来想去,用纸把一束玫瑰层层包起来,夹在腋下。
他说这个细节他记得特别清晰。
当天我在网上没找到《流亡曲》,倒是看到了《西线无战事》,便顺手买下了,只是到现在才看。

来自Wikipedia
这本书是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德国青年在法国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故事的。故事从主人公“我”的视角展开。
看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才知道什么样的细节才能触动人心,什么样的文字,从不提悲伤,却让你悲伤到骨子里。
克默里希一条腿中了枪,躺在野战医院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不可能再活着走出这间大病房了。
“我”和米勒一起去医院看望克默里希。
米勒看中了克默里希那双系带的皮靴,并暗示克默里希,这靴子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而自己需要这双靴子。
克默里希没有同意。
米勒担心克默里希突然死去后,靴子会落到卫生兵的手里,他提出要守在病房外,等着克默里希死去。
看上去,米勒非常冷漠,心比铁还要硬,在他心里,似乎那双靴子远比克默里希的命重要。
其实不是,雷马克说,米勒只是比别人更能看清现实而已。战争让人变成了野蛮人。
雷马克冷静忧伤的叙述,让读它的人很难从中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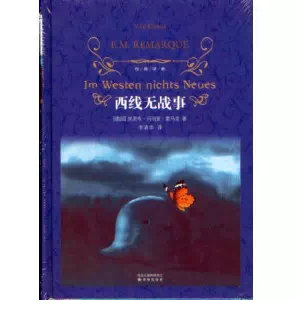
“那时我们去司令部,一个班级有二十个青年,在去兵营前,大家还兴高采烈地集体去理发店刮胡子,有的人还是平生第一次去。对于前途,我们没有固定的计划,极少数人对于事业和职业有想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生存的方式罢了。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在我们眼里,这些观念把生活和战争理想化了,而且几乎赋予了它们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不知为什么,读到这一段,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那些逝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岁月,就这样一去不返了。
读这一段,我就会想起北岛老师《波兰来客》里的一段话:“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可能就是里面的那种调调吧,关于一去不返的过去,关于破碎的现在。
雷马克的语言有一种特殊能力,有时你读着读着就笑了,但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
有一次,“我”和莱尔、恰登,还有克罗普四人在运河里游泳,看到对岸有三个姑娘款款走过,我们突然春心萌动,决定深夜游过运河,会会姑娘。
可姑娘只有三个,而他们四个。怎么办?他们决定把恰登灌醉。
可当他们三挟着面包,游到对岸,和姑娘温存过后,准备返回住处时,却看到恰登赤裸着身子,跟他们完全一样穿着长统靴,胳膊下面夹着一包东西,飞也似的向前奔跑。雷马克说,“他在全速前进。”
看到恰登“飞也似的向前奔跑”、“他在全速前进”这些细节时,就好像当时我也在现场,恰登的样子太好笑了,可当我想到恰登为什么那么奔跑时,一切又都变得悲伤了。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个情节非常重要,这应该是雷马克最想表达的地方。
“我”去侦察敌情,被“囚”在了一个弹坑,不敢冒然离开,天黑了,有个人跌进弹坑,“我”用尖刀捅死了他。
在他掉下的皮夹里,“我”看到几封信和几张照片。从照片上看,这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照片上的女人是他妻子,那小女孩是他女儿,那些信则是妻子写给他的。
皮夹里还有一本写着他姓名的小本子,小本子上写着他的职业——排字工人。
这之后,雷马克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写“我”的内心独白,写到了“我”对战争的思考,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敌人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大部分我都看不懂,实在太难了,而我只懂一点法语。但是我可以翻译出来的每个词,却像一枪打进我的胸膛——又像一把刀刺进我的胸口……”
“我”决定以后要给他的妻子写信,并发誓以后就以排字工人的身份活着,为她们而活,“我”要挣钱寄给她们,以求救赎。
遗憾的是,就连这个愿望,他都没有实现,他最终还是倒在了战场上。而当天的报纸上写着“西线无战事”。
一定有一些人是活下来的,但活着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他们。
雷马克在这本书的扉页写道:这本书既不是一种谴责,也不是一份表白。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