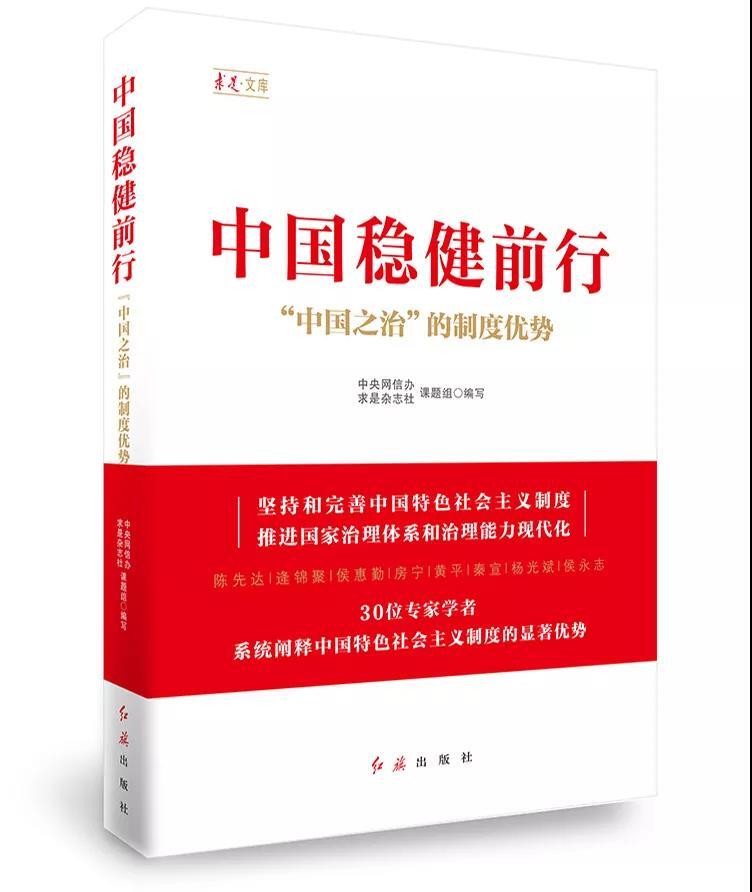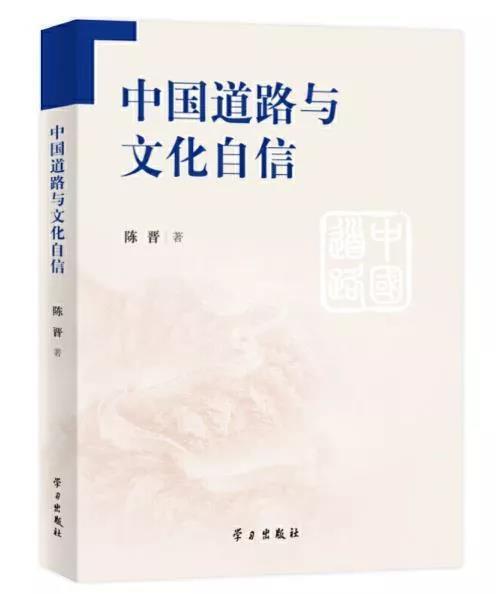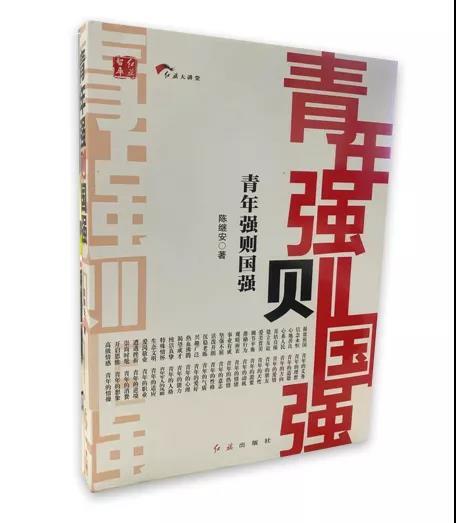最低程度的应许
2016年06月24日 14:46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兔老师
兔老师在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但是她经常走神走到不是古典文学的地方去。兔老师和阿啃和杨庆是好朋友,前几天他们一起去温州给中小学老师上课,兔老师讲陶渊明、杨庆讲心理学、阿啃讲阅读史。最后一天下着大雨,阿啃带菜虫和我们去吃肯德基,像鸡妈妈照顾一群小鸡。之后,兔老师写了这篇作文,是《一天里的四个故事》中的第一篇,那一天故事太多,平淡无奇,却有十几个。
“有时候我们无能为力。”
1
去温州讲课,阿啃和杨庆讲时,我就坐在讲台侧面,看到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事。回来的列车在雨里穿行了一千里,我们谈阿老师近来的清瘦和疲惫,杨庆说:“我担心他没有支撑”。过去十年里,他支撑了太多人,而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向他表达关切,才能不触伤我们对生活的信心。回来看见阿老师那晚的作文,写一个雨夜里独坐在绍兴街头的老者,他说:“我不能确定,那个独坐的老者,是不是我自己。”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留言说,记得在雨衣的口袋里放些打电话的钱。

2
回来第二天,倪梁找我。七八岁时我们做过三天朋友。那是大人结伴去杭州,我一路都在挑剔这个比我更小的小朋友。二十年后,我从加拿大回来当一个老师,他从纽约回来做一个记者,采访我时,忽然从记忆深处提取了那次旅行。很快他就辞职了,除了做自由摄影师外,还在我们学校兼职教25块钱一节的课,一年领5000块钱。这次讲座在一条服装街上,网吧五楼,楼梯间贴着高利贷广告。听完第一个摄影师讲他的几百张图片和社会责任、新闻理想以及为什么不得不辞职之后,我头痛欲裂。等我买咖啡回来,PPT变得干净,倪梁已经在讲了。我没有想到他讲得那么好,就像我讲得最好的课一样清晰。他讲美国摄影史上两本重要画册的图像语言,我心里涌现的,却是美国诗歌从艾略特到卡洛特•威廉斯的转变。美国诗歌史是我大学三年级的课,如何能预期十年之后会在这样的地方,以影像的语言重听一遍?

3
傍晚的奇遇是尤骏发来的消息,说在南长街演出。我穿过无数酒吧和自拍杆,在人群中逆行。夜幕之下满街都是场子,每经过一个我就停下来鉴定一番,不确定如何找到他。找到那里时,我有点发呆,因为我对民谣的想象,是在夏日的傍晚、是不插电、是不比街沿石更高的舞台、是牛仔裤席地而坐、是路人蹑声走过、是互相看见而不加侵扰、是忘掉了年龄而永远年轻的心。但是在那一人高的台下,一切都不太对。老爷爷老奶奶、光着膀子的民工、尖叫的小孩、与我一起淹没在灯光和喧嚣中。台上的歌手既看不见观众,又听不清自己的声音,只能在一片耀眼的蓝光中汗流浃背地认真弹唱,偶而向台下的方向茫然一瞥。音响没有调好,于是格外轻的口琴声便成为了唯一自由,而能像晚风一般飘来的声音。雨来的时候,我听到了想听的那首歌。但身处这个无法被看到和听到的舞台下,我不知道该不该拍手。

4
一切结束后,去看在打暑期工的凉凉姑娘。我们在凉凉漂亮的书店里喝一杯冰茶,觉得刚才没听到的东西都重新在心里听到了。凉凉扫干净书店、关门打烊,我们一起走回学校,路上她问起我自由。我想到这一切,回答说我们的梦想虽然都未实现,但却已拥有最低程度的应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