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人生半在别离中
2016年06月24日 14:59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王这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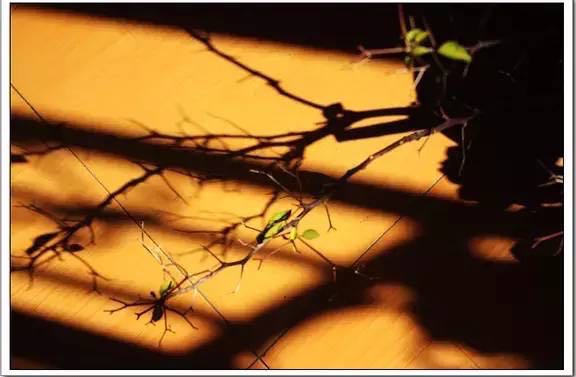
在绿妖的新书里看到她说在北京的那些饭局和酒友。乱哄哄的聚散中别有一种干净明亮,一种属于青春的荡气回肠。他们喝的酒是“小二”,北京特产二锅头的爱称。好像广大文艺中青年来到北京,住下来,有两样物事必然要沾惹上,一个是中南海,我记得焦油含量一点零的四块,点八贵点,点一的就更贵,一般都抽四块的。另一个就是“小二”。
这几年我渐渐烟抽得少,一天不过一两支,有时候一星期不沾也不想。抽也捡极淡的,中南海早在生活中失去了踪影。酒本来就不喝,酒量极浅的人往往走极端,要么怕遭嘲笑,勇于邀醉,要么避酒如虎。我是后一种。回想起来,平生仅有两次醉酒,都是在北京厮混的时候,喝的也都是“小二”。
零一年跟小早合租在南三环一栋居民楼上。十三层,二室一厅,房租总计一千五。工资三千,能过,也确实挺穷的。有一天晚上,是八月份吧,在牡丹园的一家小馆子,有人请吃羊腿,请喝酒。完了打车回到楼下,已经半夜了。应该是半夜,因为整栋楼的灯大半已经熄了。而且电梯坏掉了。只能一层层往上爬。事后小早说,爬到第七层的时候,我开始在每层楼道口的人家门前坐下,捏起拳头奋力砸门。那个夜晚让她很长时间怨念不已,作为东北人,她简直把这辈子的不是都赔完了。
现在我能够想象,在那种幽暗肮脏的楼道里,一扇扇房门向着两个醉酒美少女的脸上摔过来,关上。咚、咚的一声声巨响,确实是很无情的哦。
第二次是零二年冬天,我们所在的公司倒闭。老板拿出最后的慷慨,在上地那边一家饭店包了个厅,开散伙宴。那天所有人最后都喝高了。最先醉的毫无疑问是我。酒到半巡,他们开始对着饭店的电视唱K的时候,我进了卫生间,锁上门,一转身坐到马桶盖上开始哭。前尘往事,受尽委屈般地流泪,无论如何止不住。直到外面的人准备破门。
那是被称为互联网寒冬的一年。这个公司的老板本来在东北混黑道,副总则是X大的教授,两个人碰到一起,骗了笔投资,就来北京开网络公司了。老板是个面相阴骛一笑像只捕食瘦猫的男人,爱好除了开会之外,就是在烟抽完的时候,从办公室摸出来偷员工的烟抽。我的座位离他的房间最近,被偷的烟也就最多。一天一包根本不够抽。总是这样,最初大家都满怀信心,对未来愿景多多,但散场也是必然的。

路灯一盏一盏,沿着宽荡无人的大街亮下去
散伙宴结束的时候,也是深夜了。风大,很冷,酒很容易就吹醒了。是晴天,当然看不到星月。天真他妈的高。无限地往上方高远着。只见那路灯一盏一盏,沿着宽荡无人的大街亮下去。还有少量的车灯游曳,带着夜晚特有的车轮轻啸声。人们开始嬉笑着互相道别。轮到我和老板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尴尬中,破天荒头一遭掏出中南海,顺手给他打了一支。他一愣,忽然大笑起来,把我拦腰抱起,在空中转了两个圈,然后放下地,拍拍肩,也没再说什么。再过了几个月,春天的时候,我收拾东西回了合肥。
在合肥时,如绿妖书中所说的那样,县城也好,所谓的省城也好,文艺青年的日子总是不太好过的。很寂寞,偶尔饭局时听到有人说也喜欢某个作家,跳起来隔着桌子把手长长地伸过去相握,有一点地下党接头的惊喜。真来到了北京,也还是孤独。我没有熬过那种孤独。回到家后,又开始怀念与后悔,不过,也回不去了。年纪越大越回不去,也没必要回去了。
网络越来越发达,地域不再是对人很了不起的阻碍力量。人的年纪也在一年年增长,变老。最后,说到底,大部分中国人是跟自己的房子活在一起,长在房子里的。像一棵盆栽植物,死也死在这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相对还不算太高,一般能够承受。在三四线城市,只要你想,饭局多得你疲于应付。合肥的人喜欢在黄昏时候满街赶饭局,喜欢在饭桌中拼命地劝酒。各种据说上档次的白酒。当然,如果不是做业务,也没什么人什么事当真值得拼却一醉了。在合肥,我一滴白酒都没沾过。饭局上喝酒这回事,就像女人破处,从最开始坚决不喝,慢慢大家也就绝了念头,不来多费口舌,白送一口毒气。但一旦开口喝了第一滴,人们就会认定,反正已经这样了,别装了,给个面子,喝!
白酒闻起来香,喝过白酒的人,身上则有一种极难闻的酒臭。也许还混合着胃里饭菜的发酵气味,一个被白酒灌醉的人,就是一只会移动的泔水桶。作为不喝酒的人,想理解酒徒很难,单纯感官上就有一重重障碍。所以我也很厌恶身边的人喝酒,尤其白酒。啤酒要好一点。上一次喝啤酒也已经是好多年前了。那时候跟胖子还没挑明关系。一天下午,静极思动,就发了条短信,我们去喝酒吧!黄昏的时候就去了大排档。

是夏天,天黑得晚,可也慢慢黑了。天色一点点沉下去,夜色与城市的灯火一起,一点点升起来。凉风习习,大排档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又慢慢地越来越少了。雪花生啤,我喝半瓶,胖子喝三瓶半。都没什么话说了,低着头,一只只剥碟子里的水煮花生吃。偶尔抬头四顾,看见卖唱的人在收拾他的家伙,小音响,电喇叭,话筒,全塞进一个大帆布包里,拉上拉链,他站起身来,把包轻轻地、抱怨地用脚尖一踢,咣的一声。真是个良夜。
半辈子喝酒的次数,两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三年前,唐姐空降到合肥,看上去也挺游手好闲的,周末,兴冲冲和我们去城西一座大庙里去吃素斋。胖子哄他说素斋好吃。庙里有个老和尚是旧识,所以十元钱一个人的门票也没买,晃着膀子就进去了。找老和尚要爬一个小山坡。坡底下一棵桃树,挂了果子,已经红熟得不堪。低处的已经被摘光了。高处的够不着。地下草丛里倒藏着一只红的,大概是才被风吹掉下来了。唐姐一头栽过去,捡起来用袖子擦一擦,一口下去嘴角流汁,操,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一路走一路回味,把头点了又点说,香,全然一股天然桃子香。


下山的时候,才发现山坡上种的全是梅子。半青不黄的小圆果把枝条坠到地面上。那天我的背包被梅子装满了。回家一称有四五斤。配上三斤冰糖和两瓶家酒,我全给泡起来了。转眼过了半年,开封喝的时候,意料之外的甜香满嘴。这些青梅酒,家里来朋友了就拿出来喝一些。也就很快喝完了。到厦门阿亮来玩的时候,剩下大概还有半斤吧。他端着酒杯,耸鼻子闻了闻,尝了一尝,沉吟道,“甜了点。”然后就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一杯一杯,一边说着话一边悄无响动地全喝光了。那天中午他已经喝过一顿了。喝完这些,他就慢悠悠地提着包走了,去火车站了。阿亮是个老酒鬼。也是我见过酒品最好的人。另半个酒品好的人是叶行一,因为我从来没见他喝醉过。永远只是老实坐在那里一副能坐到天荒地老的样子,酒瓶就一截截空了。本来话就不多,似乎话更少了一点。略显出一点儿发呆样子,像一只在浮冰上观风景的企鹅。如果问他一声,他说把头埋到怀里说,我想做个有钱人。过会儿再问,还是这一句。这是婚后的情况。婚前是另一句:我要找个女朋友。

甜甜的青梅酒
后来我们没再见过阿亮。唐姐也离开合肥了。据说现在到处喝应酬酒喝得满腹风骚。叶行一带着老婆到京城找钱去了。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前些天,大概立冬前后吧,jardon寄来了几斤青梅酒与杨梅酒。jardon是未谋面的豆友,彼此关注也有七八年了。早几年他在北京种菜,卖菜,这两年跑到杭州种果树,冬天在淘宝买了著名的东北产蓝莓和树莓苗,春天来时就见他满世界慌张地打听,怎么不发芽?我回复说,可能地栽的发芽晚。私下里实是疑心他上了奸商的当。这个人我总有点担心他会破产。没想到居然已经酿出酒来了。是用大米自制的发酵酒,配了两种果子。也是古法,我翻书的时候曾经看到,宋朝人已经这样做了。我拿去送了合肥的一些朋友尝,都说很好,就是度数低了,没有白酒来劲。
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颜色好看,闻着有果子香气,喝到嘴里清爽微甜,事后身上也无酒臭。江淮地区的冬夜冷得很。过了九点,电油汀的温度终于上来了。我们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各干各的事,手头就拿这酒咂嘴。身上暖活了,人有点晕忽,软绵绵的,用古语讲叫陶然。就上床睡觉去,电热毯这时也捂得正好了。这段时间睡眠其实并不好,临入睡前那一小会儿尤其心悸。所以喝一点点果子酒正合适。

青梅煮酒
小时候听人说青梅煮酒,总以为是把梅子一颗颗扔到酒里,下面起个炉子煮它。想象小圆果子们载浮载沉,很好玩的。那酒也必然是凛冽的白酒。后来自己看三国,才知道是拿青梅做下酒菜,青梅也不是直接吃,要盐渍或蜜渍过的。煮酒不过是温过的黄酒。现代酒场流行的蒸馏酒按文献公认到元代才出现。那么之前的人喝的都只是度数极低的发酵酒了。
“何辞白酒饮千钟,人生半在别离中。”那也不是现在我们说的“白酒”。只是浊酒而已。可能度数不超过十度。所以千钟不醉什么的算不得太夸张。并不是古人的酒量就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