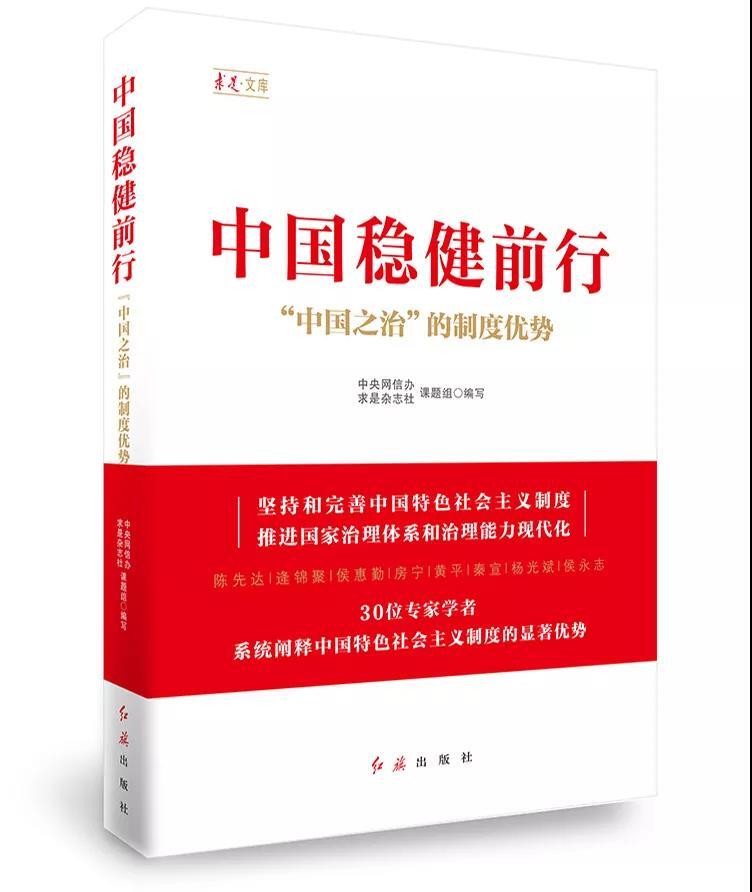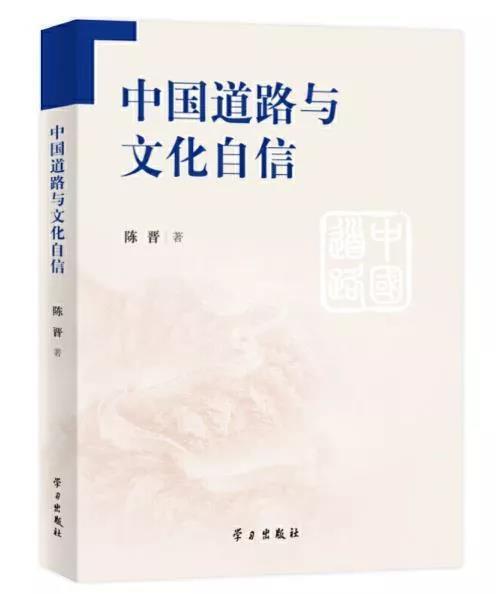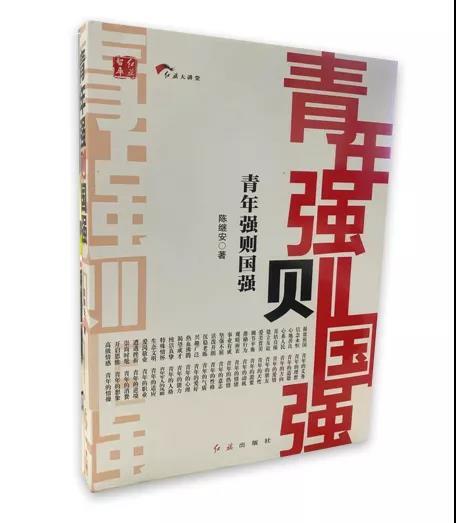张蔷,80年代我们心中的妖
2016年06月23日 17:12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郑昀
当老得只剩下回忆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坐在高墙下又不能动弹的人,你目力所及的是一片片石灰剥落下来,一块块砖降落下来,最后轰然倒下,埋葬肉与灵,成为灰烬下的白骨皮囊,而回忆至多也就是一场大雨过后的渗出物,溢于沟豁之间。
我不喜欢回忆,回忆只是时间和岁压榨下的一点点挣扎,而怀旧却不同。
怀旧是行进中的逗留,是偶尔想呡一呡的棒棒糖;怀旧是穿过麦田去听一场音乐会时遇到的稻草人,是点燃今天的柴火;怀旧是平凡日子里的调侃和撒娇,是梅雨后晾出来的一件花衫。
怀旧是对当下的一点自我奖赏。怀旧不妨碍你去夜宴笙歌,喝一掉杯杯不同烈度的酒,怀旧之后你依然可以点一大份三成熟的牛排和两盘小龙虾,怀旧不会改变你开个快车压个实线闯个红灯,怀旧不能阻挡你从午夜的机场出来去奔赴红唇烈焰的约会,怀旧只会让你累得躺下的时候心依然在远方。
约么?去喝一杯,说好了,只怀旧,不回忆。
80年代,不是每个男生一定有牛仔裤,但是耳边一定飘过张蔷的歌声。
80年代,整个中国开始发出酒曲和米碰撞的气味。
每个青年的心都是漾漾地收不住的样子,扎入人们心中的不完全是外来的光怪陆离的物质,更多的是自由而荡漾的空气,一切都在告诉你所有过去“不可能的可能”将雪崩般地到来,内心的妖怪在等待一次百年大赦。
当很多人还在矜持或者假正经,还在和自己心里的妖怪斗争,还在女孩的小短裙面前别扭的时候,张蔷已经如一树蔷薇开得疯、开得痴。

八十年代的张蔷
一直以来我总是从声音去臆断这个唱歌的女孩是香港人,或者至少是广州人,因为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中国文字,竟不知道这种文字可以用来如此热浪而作嗲地唱歌:句子可以突然咽气一样地断,吐字可以在这么多曲曲折折后收,腔调可以如此上上下下地摆。过去的女人总是在台上唱歌的,而这个女人却是贴着你的脖子根唱歌,嗲和狂直刺你耳膜后面的位置,那些位置是不受意志控制的位置,是人的私处,她把人撩拨得如同被吹大的橡胶套套。
80年代,地摊上出售的磁带封面总是四色错乱的,红黄蓝黑永远不能够叠加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张蔷的爆炸头、涂着深色眉毛下的大眼睛和露出一点微微耸着的肩,反正已经洋气得让人晕了。一直到开始怀旧的年纪我才大梦初醒似地发现这张蔷完全是个北京女孩,一张典型的北方蒙古族大脸,眼睛长得高得快顶到额头了,眼睛和嘴之间是一大片开阔地和颧骨,面泛红色油光,那红是少年冻疮般的红。一霎时,我真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起在欺骗我。
不过你得承认回忆总是那么靠不住,就像回忆中女神的样子总是美图秀秀一般,但是张蔷还是张蔷。

张蔷还是张蔷
凡是经历过80年代的青年只要你试着闭上眼睛回到那个时代的摊位前面,熟悉的气味和声音就会清晰得如同你穿过的第一条牛仔裤一样,你可以在想象中抚摸出每一条纹理和经纬。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里除了响遏行云的邓丽君之外,张蔷就是的邓丽君之二。她比邓丽君多了狂野和放纵,如果邓丽君是上沪上小菜的话,张蔷是海鲜煲仔饭。
张蔷翻唱的大部是港台歌曲,而港台歌曲大都翻唱自日本,所以张蔷的歌曲很多年之后我都在日本歌手的经典曲目中听到了。张蔷有两支歌最火,一支是《月光迪斯科》,迪斯科是80年代的国际歌、是时代的号角和太阳:
没有七彩的灯|没有醉人的酒|我们在月光下|跳一曲,跳一曲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
很多次我在百度上搜索这首歌的音乐和词作者,但是一无所获,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应当有机会向他们致敬。张蔷的另外一支歌曲是《好好爱我》,作曲是岛村叶二,凤飞飞唱过。
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的待我。
这一类歌曲张蔷唱得很多,《那天晚上》、《害羞的女孩》都是,一点点矜持背后的任性和放纵,就是这么打动人。

张蔷的专辑《青春多美妙》
张蔷是个大嗓门,那个年代的青年是可以流氓但不可慵懒,可以打架但不可伤感的,所以张蔷唱歌的方法基本上是往上扯,扯到不能扯的key时就用滑音,而配器基本就是“蓬兹,达兹,蓬兹,达兹”。张蔷也唱过一支弱弱的小女生类型的歌,歌名一直没有想起来,只记得开头的句子是:“是你推开了门,我才知道爱的是你。”中间有一句“嗳,嗳,嗳嗳嗳嗳”的过门,嗲得很干净,很淡的旋律,雾里飘来的感觉。
张蔷是80年代的地标性建筑,据说她出过30多个专辑,2500万张发行量,创造了世界流行歌曲销量第一,无人可敌。我想事实上张蔷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字,当年每一台双卡收录机都有翻录功能,谁买了一盘带子至少会被借去翻录十次,虽然每一次翻录都会让她那嗲嗲的翘臀似的柠檬味的甜腻的声音变得更加沙哑。

张蔷的专辑组
盒带是会被卡的,卡住的盒带被小心地从录音机里拖出来,像一条肠子,实在卡的厉害的地放只能剪去一小段,然后用胶带沾上,每次走带到接点的地放声音就会一跳一跳。1985年,我在北京隆福寺的地摊上逛,第一次听到张蔷的《相思河畔》,我停下来听,在“我要轻轻告诉你“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得粗而慢,在一阵鸣鸣声后停止了。后来我化了大概5块钱买下了这盒带子。
磁带、牛仔裤和太阳镜是当时集市上的三大主流产品,磁带是可以复制的,牛仔裤是80年代的流行标配,是今天青年的爱疯。地摊上的牛仔裤紧身居多,尺码混乱,没有男女款式之分,越紧越好,地摊边半拉半开的布帘子后面,总能够看到使劲往胯上拉裤子的女生,而男生在拉的同时还得拼命地往裤裆里塞小鸡鸡。想起这样的场景就会有《月光迪斯科》的调子跟着出来。
张蔷是个始终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歌手,那个时代歌手也没有很多收入,据说后来她只能黯然离开北京去了澳洲。

凡是我们反对的敌人就会拥护,1986年4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做了张蔷的专访,他们评价她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
几年前在CCTV《见证》的访谈中张蔷第一次在中国的中央媒体上出现,澳洲归来经历世事的张蔷已经不再是那个傻傻的北京胖妞了,身上透露出很高级的气息,毕竟少年时期是跟着北京电影乐团的小小提琴手妈妈学提琴的。访谈中她说她依然热爱唱歌,嗓子没有任何变化。
我的手机QQ音乐里收了她的三支歌曲,其中有一支是新歌《我们的80年代》,旋律是旧式的,现在听来有点闹,她在歌里唱道: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我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