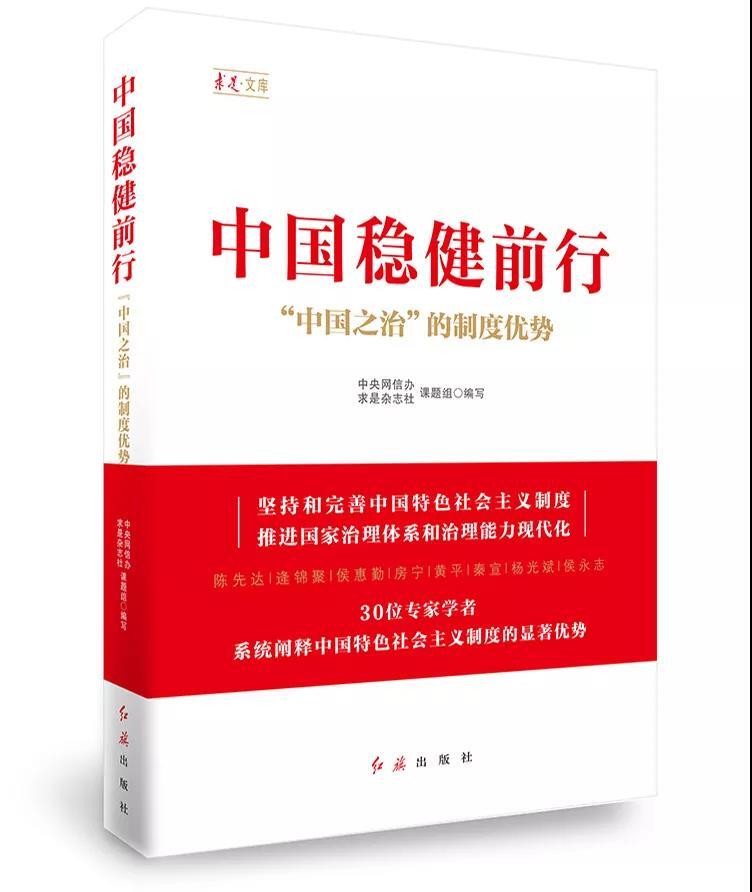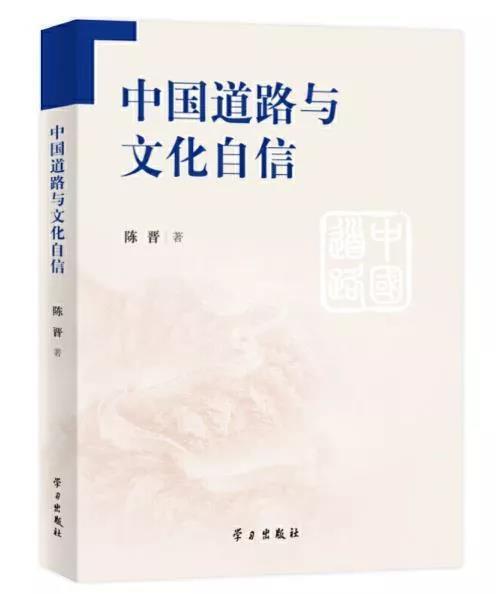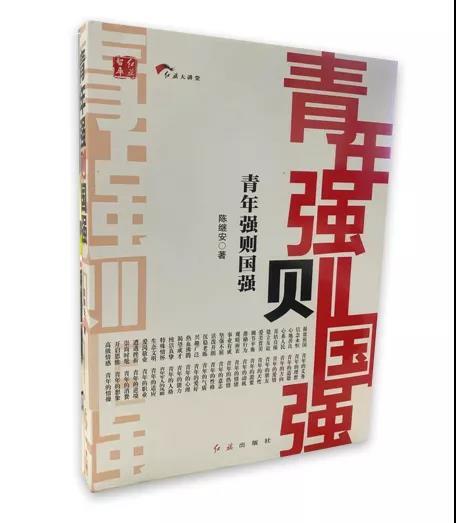不雷不鸣丨我的兄弟们
2016年06月14日 10:01 红旗出版社官微-左读右涮 聂磊旻
羊皮的筏子喝醉的城,西北的风沙带刀的河。秋风起,江南的矫情就再也忍受不下,一气流窜到了西北偏北的兰州。沿途一路扰袭天水、成县、武都——做一个为期一周的农村调查。翻阅了当地的地图和县志,发现这居然是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此时,正裹着羽绒衣在降温的兰州城吃面,电视机里正直播中国男足对阵马尔代夫队——本来,我应该和我的兄弟们一起在更冷的沈阳战斗。最近一段时间,体育记者的命途似乎很受关注:阿里巴巴成立“阿里体育”,前体育记者、网易副总编颜强辞职,朋友圈频现“牛B的体育记者去哪了”的新闻……如此密集的关注,让体育记者这个群体受宠若惊。这么多年,体育记者终究是边缘,在报社地位类似“宋兵甲”:边关战事急,大将单挑,你连在边上摇旗呐喊的机会都没有;集体冲锋,你执鞭坠镫跟在队伍后面,连个脸都露不了,往往在第一集时——应该是谈版会时,就被砍掉;马放南山全国放假,这回露脸了,站岗放哨填版面,和娱乐、本地新闻的兄弟们一起过年……2.体育的附属地位决定了体育记者的角色扮演。“战士责任重,妇女冤仇深”——每每和兄弟们酒后感慨,总会情不自禁想到《红色摇滚》里的这句唱词,也算自我解嘲。如果把财经记者比作一群穿梭财贵的武陵年少,社会新闻记者是仗义执言的市井豪侠,调查记者是一击必中的孤独杀手,那么体育记者就是一群骑快马、喝烈酒的江湖刀客。记者收入不高,体育记者尤甚;记者四海飘荡,体育记者更能吃苦,而且相较其他工种,体育记者更是看重江湖情谊。每逢国足主场打比赛,全国足球记者都朝一座城市涌将过去,此时当地的媒体兄弟便按照规矩在赛前安排一场比赛,然后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顿酒。数十人的服装、场地、对手、大巴车、矿泉水、就餐地点……事无巨细,当地的兄弟都会安排妥当。去年国足在南昌打新西兰。按照惯例,发了装备,踢了比赛,晚上南昌的媒体兄弟又自掏腰包请大家喝酒。没想到,他们在酒店门口还拉了一条横幅——“欢迎全国媒体兄弟来南昌采访”,走进酒店大堂,大屏幕轮番滚动欢迎致辞,让一帮刚从球场下来的草莽很是感动。由于三十多号人马吃酒,老板随即清场,把数张桌子拼起来——梁山泊上喝酒也不过如此。08奥运,全国体育记者达到鼎盛时期。各路兄弟抱团成风,早报团、晚报团、网媒团……互相提供资源、讨论业务,一度让上锋担心兵变,不得不强令解散。虽然如今老记者都逐渐退出江湖,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的“八千足记卷平冈”的盛况已经不复,但是江湖上的那份情谊还在。冲州撞府,一路疲惫,就地找几个当年的兄弟喝酒叙旧,那是体育记者最擅长和开心的事情。3.体育记者有才华。以体育记者身份扬名的人很多,最早的“舞文弄墨”,龚晓跃、刘原、李承鹏,如今都是跨界的文字高手;国内第一编辑魏寒枫,10年前“转会”《体坛周报》的“转会费”就有70万元;黄健翔、刘建宏、詹俊等解说界的体育人士更不用说了,后者目前年薪据说高达500万。体育记者不矫情。商业比赛时,梅西住得最好的涉外五星酒店,我们能住;采访户外运动时,帐篷、牛粪、12天不洗脸,我们也能适应;奥运会、世界杯的开幕式我们能去,翻墙爬窗进乡村小学采访的事我们也干……体育记者能吃苦。这些年单单写稿的地方便五花八门,像什么颠簸的汽车上、嘈杂的发布会现场、大雨如注的看台……那都不是事,济州岛红灯区后面的垃圾箱蹭无线、人迹罕至的小岛上找电源——2010年南非,我和深圳晶报的吴邦在球场外面的荒野等车,他急着发稿,自顾自就坐到泥地里。恰好漫天黄沙起,那场景就像民工兄弟讨债未遂,心酸无奈一屁股瘫倒在地。去年,老东家来了位新同事,小姑娘为了赶稿子,还在“外婆家”的厕所里敲了一篇——我后来强烈建议她去优衣库的更衣室也写一篇……如果有机会,以后会写一篇《这些年我们写稿的地方》,估计也很欢乐。体育记者是个特殊团体,如今不少兄弟选择了辞职。和别的行业不一样,我们不矫情。走就走了,留就留了,扯什么情怀、梦想、守望,江湖上有兄弟,走哪都有情谊。等到那一天,摔杯为号,杀将出来,我们还是一群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