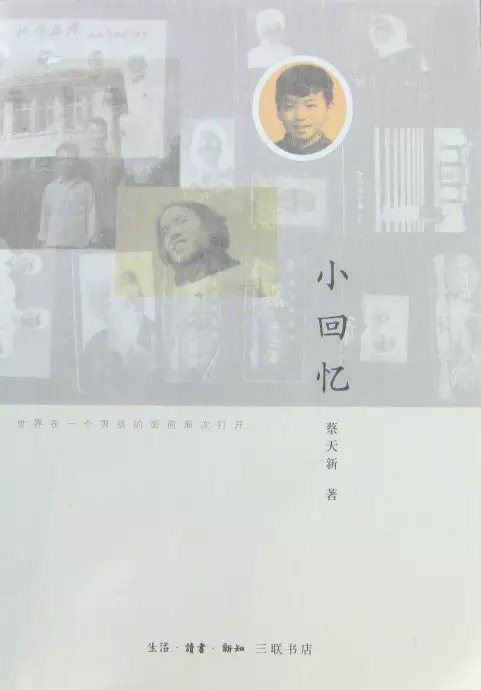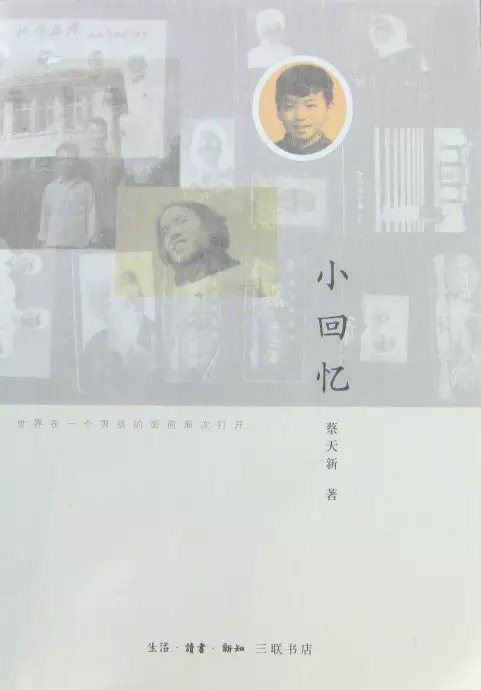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马年春晚王铮亮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戳中了好多人的泪点。背景放的是一个女儿和父亲30年的合影,女儿越长越高,越来越漂亮,而曾年轻帅气的父亲,渐渐老了。节假日就是陪亲人,孝顺,就是都顺着老人,虽然他们的唠叨听了几十年,张口上半句,下半句就能接上,听听都累,但也要忍着,因为不想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父亲很传统,是我完整童年的重要部分,他不是一个爱唠叨的人,男人么,轻易不流露感情。我与他的合影,屈指可数。他走了7年多了。他走后头三年,会经常出现在我梦中,拿着盛热腾腾红烧肉的保温瓶,却怎么也送不到我家,醒来想想,因为父亲走得早,还放不下对家庭的诸多牵挂,所以在梦中拼命做事体补偿我们。2006年12月31日一早,他弥留之际,已经什么话都说得很艰难了,肝昏迷。回光返照的那一刻,他开口说的竞还都是家常:“澜澜,看看屋里厢的面包蛋糕券有没有作废,今朝是最后一天了。我袋儿里还有一张知味观的卡,还剩50多元,倒是不会作废的。”停了半晌,他呼出很重的一口气:“今年过年,你们要重新安排了。”断气的时候,是18:35,女儿刚从学校迎新晚会上表演回来,我们把她接到医院,脸上还挂有油彩。不懂事的女儿在五六岁时候最爱问:“外公,你什么时候死啊?”到了外公真的死了的那刻,她没事人一样没有流一滴泪,在5天后的追悼会上,她突然无声地泪如雨下。而我,在冰冷的冬夜,拥被发抖。我爸爸的发小陈文海伯伯在他临终前几天来看他,俩人说了一小时的绍兴土话,他们是挑着行李扁担到杭州讨生活的“道伴”,头碰头,脚碰脚,子女年纪也差不多大,我只听到父亲反复说:“太快,太快了……”他的肝癌从发现有肿块到去世,只有21天,他69岁。不是检查不出来,20多年的老乙肝渐变到肝癌也是想得到的事,但他会忍痛,痛到受不了也不和我们说,直到2006年11月,有一次去接我小学4年级的女儿放学,不由自主摔了一跤,膝盖都流血了,才和我妈妈感叹,体力不如从前了。因为频繁起夜小便,怀疑前列腺有问题去看医生,没想到拍了片子出来,大问题是在肝上。那天上午我先陪他挂号,后来单位急等我开会,我就没有等到拿片子,我爸说他等着拿吧,后来……后来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捏着那张判决书,从浙一挪了半小时挪回家的。一开始他积极地等待手术,但专家反复会诊,说是动刀迟了,只能……我们的神情瞒不住他。绝望彻底把他击垮了。父亲学历低,是个高中生,偏偏分配到北大清华高才生扎堆的水电设计院,他不服气,做什么都走在前头,苦活累活,拼了命做工作。从艰苦田野作业的12年水库勘察队员到两次总共4年的援非,乙肝就是这样在多哥修水库时染上的。性格即命运。他的笔头功夫很灵光,图纸也画得很像样,干净漂亮,在院里勤恳一辈子,最大的官当到院办主任。吃亏在学历低,就上不去了。有时候在单位累极,他就在家冲我们子女发火,他是属虎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那种。和他同在一个单位上班的妈妈说他有些郁闷。他奋斗了一辈子,心气也高,是个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人。他是一代30、40后父辈的缩影。我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是他的某种安慰,他相信我是遗传了他的才气。每年为我做剪贴簿,就是把各处发表的文章整整齐齐贴到一本档案簿里,线装本,这样的剪贴簿我有10多册。我评正高的时候就是他帮我准备了一叠材料的。世界上最疼我懂我爱我的男人是他。时间去哪儿了,父亲就去哪儿了,伤痛被时间的流沙慢慢冲平了。这几年父亲越走越远了,偶尔才会到我梦中剧情里来客串,栩栩如生。我母亲说,现在平时连个吵架拌嘴的人都没有,冷清啊。她73岁,刚刚过了本命年,老话是本命年要佩玉保平安,带了一整年的玉,在大年初一这天,才让我解下。她的信念是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参加我女儿的婚礼。小学老师出身的她比我父亲乐观得多,对生活的看法简单得多。人生忧患识字始啊。自父亲走后,每年回老家走亲戚迎来送往的差事,就这样接棒到了我们表姐表妹和我这一代。我妈妈习惯了依靠。作家们笔下的父亲是怎样的呢?我随手从架上取下浙大数学系教授兼诗人蔡天新的《小回忆》。其中有一篇《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壮志未酬的西南联大学生,在家乡的县中教书,文革中进了校办模具厂做木工,退休前是黄岩中学副校长,在天新10岁之前并不在一起生活,所以他对父亲的印象比较淡漠。在天新读大二的时候,他父亲被查出胃癌,1980年5月去世。天新对父亲的印象是:“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怀着兴味,听众幻想的劝告/一双因患冻疮而肿大的手/在白色的窗帘布后出现/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一片痰紫色的幽远/被一个感觉的鼹鼠丘破坏/像一座石板地的旧式楼房/以此伤害了黑夜的眼睑/一把精心制作的扶手椅/和一个并不丰富的藏书架/回想之翼的两次扑动”。这首诗里出现了他父亲新手制作的两件木质家具——藏书架和扶手椅。
这是天新在父亲去世13年之后给父亲写的一首悼亡诗,我觉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感情还是粗糙了一点儿,即便是父与子。女儿真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儿子呢,更多时候是墙上一张肖像画,看得到,摸不着。在人类社会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中国或外国,对亲情的怀念和遗憾一直都会经常发生。从生理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孩子都有需要和想念父亲的时刻,无论这位父亲现在是否与你生活在一起,无论他是否伟岸或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