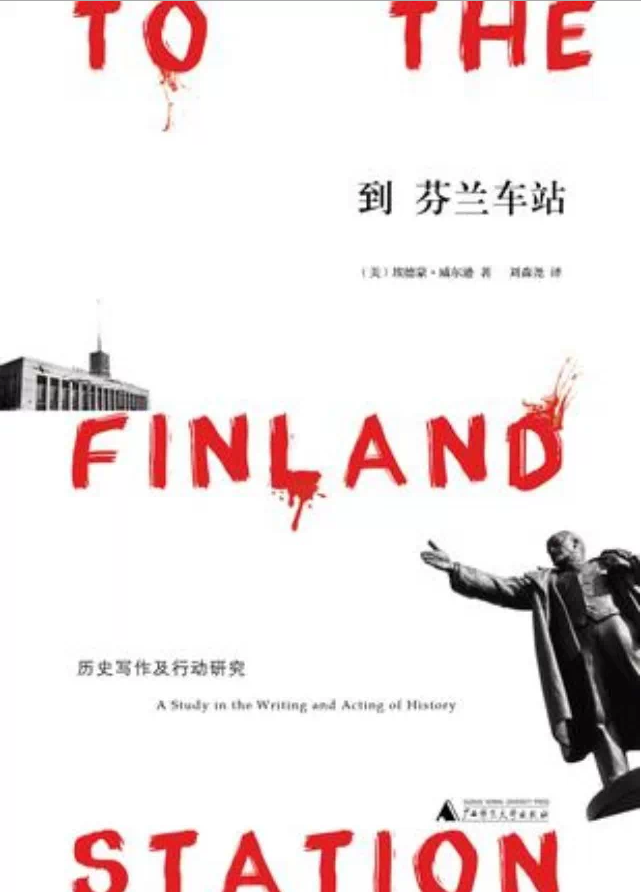一段历史的浪漫之旅
2016年07月15日 10:59 蒋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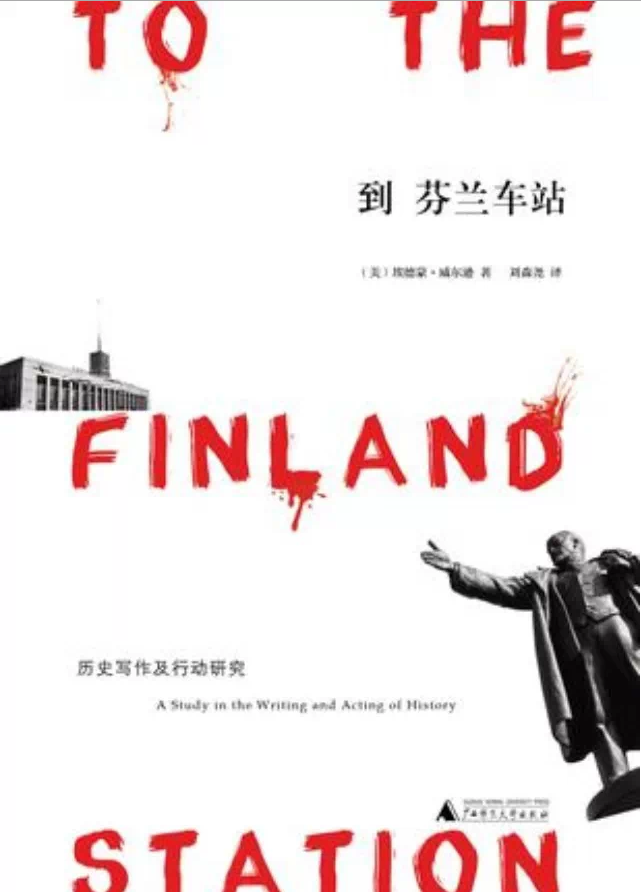
【刚刚做编辑的时候,八圈曾经在酒桌上羞赧地向江弱水约稿,蒙他不弃,将稿子给我。但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在我社出版而改投其他社了。八爷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遗憾。
作为本书的序,江弱水在《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中是这么评价《到芬兰车站》这本书的:
读这本书,像观赏一出连台大戏,剧中人物一个个走马灯似的登场,有舞台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也有跑龙套的拉萨尔、巴枯宁、蒲鲁东。威尔逊采用焦点式的叙述和戏剧性的对比手法,巧妙呈现他的人物,好像经济学家图表上的曲线,在时间中来回穿梭走动,文笔酷似他所赞的米什莱,有一种荡气回肠的交响乐效果。威尔逊拿手的批评性叙事,变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书中发挥无遗。他复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时征引逸闻和趣事,随处穿插细节和场景,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高潮来了,又掐断了,织入另一波起伏中。
让我们来看看作者蒋雯如何评价埃德蒙·威尔逊这位“知识上的纨绔子”(奥登语)这本关于历史和历史行动的书。感谢蒋雯授权左读发布。】
历史的学习和阅读多来自于文字的记录,偶尔能够遇到直观性的材料,可它们的真实性往往又是有待考证的。当我们从千篇一律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寻找历史时,埃德蒙·威尔逊,这位自由独立的美国文人用他敏锐的洞察力开辟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展现历史。在他的文本里,同时包含了历史两部分的内涵,即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和记录处理历史的文字资料,也即小说的副标题所标示的“历史写作和历史行动”。
正因如此,历史也就成了威尔逊这部题为《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的小说的主题。从历史写作与历史行动两方面看,威尔逊将人类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共产主义观念的诞生,它的起源、产生过程,通过历史人物的历史写作、历史创造和历史行动,加上他独特的写作风格真实地展现给回味历史的读者。
历史写作、历史创作、历史行动也就分别构成了作品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剖析了米什莱处理法国大革命的方式和勒南、丹纳、法朗士对历史的写作;第二部分通过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安凡丹的空想主义思想引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展现他们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创造的伟大创举,是作品的重点;第三部分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历程,就是纯粹的历史行动。而到达芬兰车站是全书的高潮部分,是通过漫长的无数人的历史写作到达的历史行动。
在埃德蒙·威尔逊的自序中,他如是言道:“本书主要想探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如何发生……”我想,列宁乘坐火车,穿越茫茫的中欧和北欧地区到达芬兰车站的那一刻,便是作者所说的那个“突破”。因为“1917年的列宁,带着用辩证法包装着的维柯的上帝的残余,不用害怕罗马教皇或新教大会,也不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四季控制机车载他前往彼得格勒这么简单,他估算他的机遇精确到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伟大时刻的前夜,人类第一次,手上握着历史哲学的钥匙,要打开历史的锁。”由此可见,在威尔逊看来,历史写作就是为了形成历史行动,这也就是威尔逊萌生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他认为行动的意义大于写作,阻止文学成为行动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曾因它的文学气质多于政治气质而遭到批评和质疑,但浙江批评家江弱水先生却在其《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中称赞“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的文学气质”。威尔逊的这部作品是关于社会主义观念、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形成的,其主体是随处可见的交迭穿插的历史事件、深邃玄奥的哲学思想、严密而有逻辑的思想体系,这些内容的阐述往往充满了学院派的味道,让人立刻联想到学识渊博的学者及其术著作。但威尔逊以其灵活多变的创作习惯和独特自由的思想将严谨的历史、哲学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呈现。
路易斯·门德发表于《纽约客》上的《历史的浪漫——爱德蒙·威尔逊的共产主义之旅》说威尔逊“清楚地看到该主题中所包含的小说成分”,并且“为它的挑战性所激动”。这部小说的灵魂是历史以及作者以此小说想要表达的他对历史写作与历史行动的看法与态度,但作者却以小说的形式,将列入历史文献资料的历史人物、历史时间、重大历史活动,结合人物身世、社会背景等,轻而易举地串联成富有趣味性的生动形象的故事,并且以火车最终顺利到达芬兰火车站,寓示形成共产主义信仰这段历史的浪漫旅行,通过写作,最终创造了历史行动。显然,这是小说的一大看点。
该书的又一个鲜明特色便是它的真实性。作者威尔逊同样在自序中提到了多则证据,证明关于列宁形象在以往资料和作品中被苏联官方过分美化,删去了颇多涉及真实的列宁性格的文字。作者为了完成此小说收集了海量的信息和资料,尽可能全方位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并以此说明“本书应该可以看成是一些革命家自认为在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忠实记录”。正因为如此,埃德蒙·威尔逊才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没有“学究气”,而是集各种理论和精辟独到见解于一身的评论家。
对于这部作品中所涉及的苏联历史文化和正在发展着的新的理论,威尔逊具有深厚的积淀。出于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在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很好地掌控着苏联经济,并且在西方经济持续大萧条的情况下,苏联经济反而得到平稳快速增长的好奇,西方学者越来越关注苏联无产阶级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威尔逊也学习俄文,阅读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深入社会最底层,调查记录经济危机下人们的生活情况、心理状态。同时,以批评家、社会评论家为主要身份的威尔逊,素来以独立而诚实的价值判断为批评尺度,真实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使他能够成为美国屈指可数的重要评论家之一。另外,《到芬兰车站》当然也延续着一个作家的秉性,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具有生活气息的人物。
还需要强调,在小说中,从芬兰到俄国的终点站显得格外平凡,甚至可以用破旧来评价。时光悄悄地流逝,火车站至今仍有静坐等候旅程结束和开始的旅客。有意味的是,芬兰火车站,为一段历史的旅行打上了标记,但历史的脚步仍在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