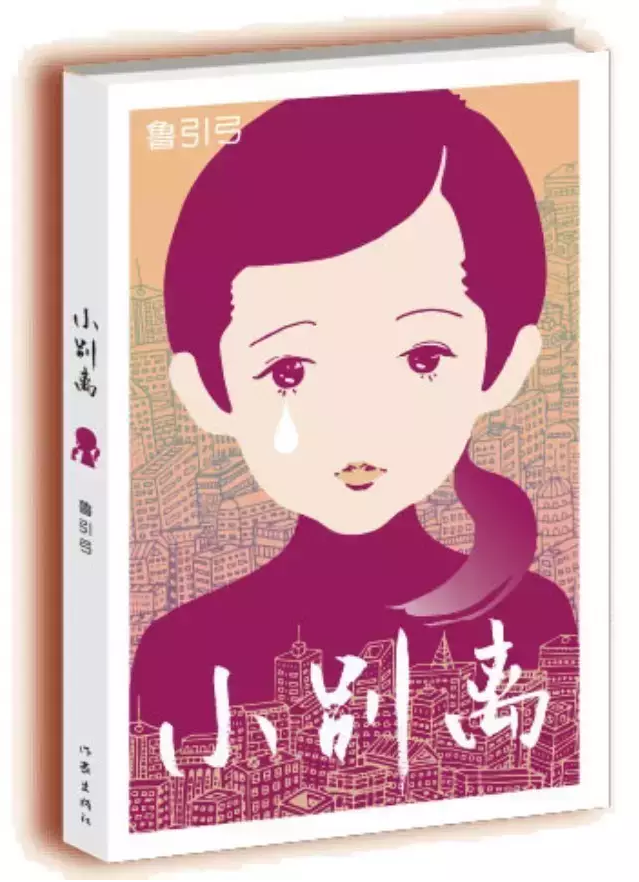《小别离》鲁引弓:像木刻一样写作
2016年07月15日 11:08 鲁引弓 袁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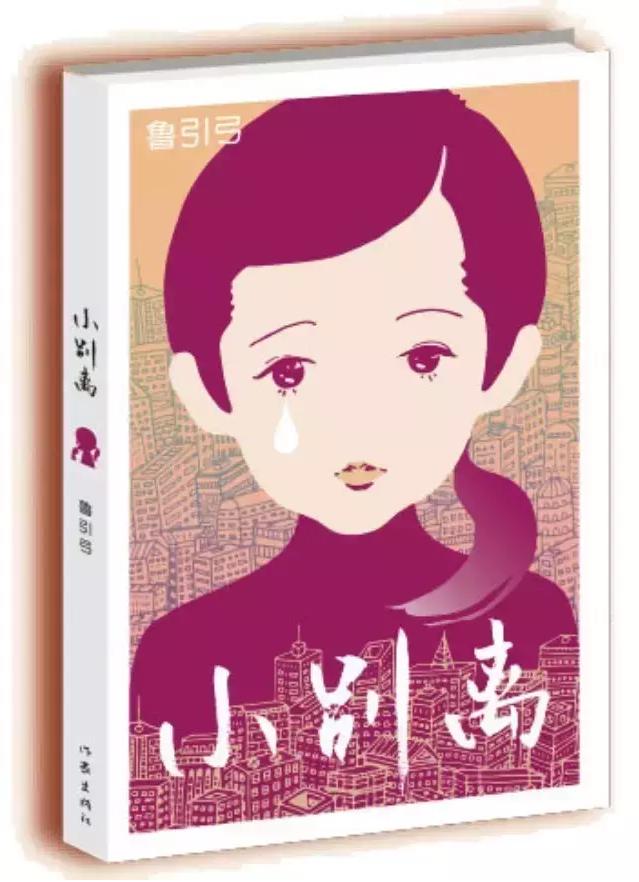
《小别离》
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作者:鲁引弓
书名题写:韩寒
【长篇小说《小别离》在2014年第2期《江南》杂志发表后,因其所直面的中国教育现状而引起媒体关注,钱江晚报3月16日以3个整版篇幅、3个系列主题“小别离:被留学潮映照的纠结现实”、“小说里的别离,看过来都是教育的焦虑”、“现实里的留学潮”聚焦该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生活选择和他们背后深刻的社会主题。
鲁引弓,男,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资深媒体人,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红旗出版社总编辑,现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在新闻工作之余,近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文学》、《江南》、《收获》等杂志发表《爱情套餐》、《少年捉奸队》、《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姐是大叔》、《小别离》等作品,取材视角独特,被影视界看好。】

鲁引弓:像木刻一样写作
访谈人:
袁敏:《江南》文学杂志主编,著名出版人,发掘了韩寒等著名作家
鲁引弓:媒体人,作家
鲁引弓,本是资深媒体人,从去年开始忽然一头扎进书房,洋洋洒洒折腾出了几个长短不一的小说。看似“玩票”,发表后,却引发了一系列让他目瞪口呆的事件,半个月内至少有6家影视公司找上门,甚至有的公司制作人仅仅看了某个作品前面的三个章节,就拍板要签约。
一位刊登过他作品的杂志编辑说,“很多人觉得纯文学没人读了,实际上,但凡触及社会话题、接地气的题材作品,仍然被影视圈牢牢关注。比如鲁引弓写的《小别离》除了谈留学教育,还紧扣中国的环保问题、食品安全等等现实。这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也是它跟很多自娱自乐的文学作品最大的区别。”
而他最近完成的《笨男孩》、《放学路上》、《我的纸牌屋》,更直击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会成长、安全、职场规则等话题,势必引起更大的关注。
问:算了一下,近一年你写了4、5个作品,其中好几个还是长篇,怎么做到的?
答:快的时候我一天写1万5千字。这种快是不由自主的。
问:许多人年轻时都有过文学梦,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消退了。
答:我也很奇怪,我一直在媒体工作,做了20多年了,一直在观察,在吸收,可以说始终处在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中。可能有的人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而像我这样的,偏到了这个年纪,才觉得要表达了,而且,这种愿望来得很强烈。人家都收山了,我反而要出山。
问:为什么呢?
答:我想最主要的是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空间上的压力,仿佛周围在被慢慢地填充起来,逼得我非这样做不可。
问:我想你是一个对社会变化很敏感的人。
答:其实我特别反感把作家想象成一个宅男。当然,应该有这样的作家吧,就是坐在家里想啊想,可能也写得够好的,但这样的作品很难打动我。尽管我的文字也未必能打动每个人,但至少,我觉得作家试图去应付的,应该是更大的一个局。如果没有这个大局,只是挖掘内心,也挖不了多深。
问:这和你作为一个成功的媒体人的身份有关吧?我们知道,你做过很多影响了所在省份的报道,比如《和外乡人一起跳舞》、《思想是怎样松绑的》,等等。
答:在媒体工作,你天然地就和现实走得很近,天然地具备敏锐、善于观察和发现这样的优势。这也是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每天都要在无数的信息中捕捉那些大家关心的,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事件,否则读者就不会买你的报纸。这其中的传播和接受的关系,我想新闻与文学之间是相通的。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个给孩子和家长看的小说《放学路上》。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的放学路越来越长。这本来是一条孩子成长的路,但我们的家长常常会担心这条路。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就和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纠缠在一起。我用有点幻想的笔法写了一个孩子独自回家路上的各种遭遇,算是西天取经这个原始母题的当代现实版吧。
《笨男孩》也是,笨男孩和聪明姐的关系,隐含着的是许多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那个男孩一直在追那个女孩,那个女孩总是跑在他前头,他怎么追都慢了一拍。里面写到了股票风波、下海潮、官商等等,最近二十年的种种变化,我们不也常常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惊慌失措吗?
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于抓各种社会热点和现象?
答: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果一定要说抓什么的话,我更愿意表述为抓纠结。这种纠结肯定会和当下社会的热点牵连在一起的。这种纠结是普通小人物的纠结,我写的都是普通的人,我们不得不置身在这个社会的普遍法则中,无从逃避。
这里我有一点体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要特别真诚,要有挑战底线的勇气。这才有冲突,才能把矛盾激发出来,才有好看的小说。《笨男孩》的女主角,你可能会觉得违背了许多常情,许多伦理标准,但这就是现实。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甚至超过我写出来的。
问:你一定是被那些事情直接打动了,才会去写?
答:是的,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打动我,我不会动笔。写《放学路上》,因为我确实遇到了那些匆忙行走在路上的学生们,包括我的女儿。也正因为这样,我写得很快,如果一个月还写不完就不写了。我不知道这算缺点还是优点。反正我感觉到不尽快写出来,自己的状态也会涣散,激情就过去了,就不想写了。结果就是,作品会比较粗线条,但人物的情绪比较强烈。
我自己觉得这有点像木刻,黑白分明,但不是那么精雕细刻。有趣的是,影视公司会觉得我的文字节奏轻快,比较时尚。他们的编辑非常看得下去,愿意将这样的东西呈现在银幕上或者荧屏上。对我来说,这完全不是刻意为之的。这里有个悖论,这几个作品传达的情绪其实都是挺沉重的。
问:我读《笨男孩》,就有种什么东西在砸下来的感觉。
答:写得最多的那几天,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我都有点发抖。每天写1万多字。劈头盖脑地把故事往前推进,现在让我回头去写肯定写不出来了。
这里涉及的其实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而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冲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一套活法。这样一来,冲突必然难以避免。
问:在你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不少论断式的句子。
答:是的,会有不少。这可能也和我以前写时评,包括采访新闻,常常需要快速判断有关。遏制不住的有各种的思考会涌出来,而且我原来学的是文艺理论。我曾经为此犹豫,但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契诃夫啊,其实他们常常有大段的议论,哈哈,所以我的心理障碍一下子克服了。
甚至有的朋友读了我的那些作品,留下强烈印象的反而是其中的议论。我想,我们的作品不可能是完美的,都只能在局部上有所发展。议论说不定就是我的一个强项,思想啦、敏感啦、直觉啦,这些也是文学的一部分。
既然是我的特点我就得认。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东西变得不生硬,有光彩。哪怕以后那些故事、人物都被人忘记了,但其中有几句妙语被人记住了,不也挺好吗?
问:据我所知,《小别离》、《姐是大叔》等作品,现在是由曾经制作过《蜗居》、《悬崖》的团队等在做,之前多家影视公司还争夺得很厉害。原来写作的时候,考虑到影视改编的元素吗?
答:还真没多想,但可能将来会想得多一点,哈哈。我其实也没写几个作品,几乎每个都被延续产品的行业给盯上了,不管是电视、电影,或者漫画什么的。十多年前,我的第一个作品《我和上一代人的战争》开始,就这样了。像海润、橙天娱乐,当时都是行业里的翘楚。也就是说,这些作品还有继续开掘的可能性。
我想,这主要是产业链不同的缘故。影视的这个产业链明显比文学出版要大。电视剧的版权,一上来价码都是超过六位数的,都快赶上我稿费的百倍了。12万字发表在杂志上,稿费也才一万多元,一个字最多一毛钱。还有家南方的影视公司提出如果作者本人改编的话,至少付给剧本费每集10万元。
影视肯定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但这或许是作品是否接地气的一种标准。
问:能否总结一下此时此刻你对文学的基本理解,或者说你的作品最大特点呢?
答:有悲悯心。我刚刚完成了一个长篇《我的纸牌屋》,说的是职场的故事,但重点不在于那种潜规则啊,你一招我一招啊,机巧不是重点,重点是悲悯。上班现在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很多人觉得不爽。我们能不能以“开心”作为坐标,可不可以?里面讲了三五个职场的中年人和年轻人,都有这种困惑,有些是扎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的,比如,为什么做人比做事更重要。我都尽我所能进行了狠狠的思考,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它,否则我们会纠结,我们的下一代还会继续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