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声的提琴
2016年07月11日 17:30 章文洁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低音提琴演奏家。“他”的父亲是一位专制的公务员,母亲则是一位极具才能的吹笛手。他崇拜母亲,母亲爱着父亲,而父亲喜欢的则是他的妹妹,因此他在家里却是无人疼爱的。因而出于对父亲的恨,以及对母亲的报复,他选择成为一个艺术家,也选择了最为笨重、最为丑陋的低音提琴。
和杜普蕾一样,他的一生也奉献给了一样乐器,所有的时光都和这样乐器连结在一起。“他”又是一个怯懦的人,自十七岁学习低音提琴后,在弹琴的十几年间,他对低音提琴产生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他碌碌无为,他不得志,但是他将自己所有的不如意都怪罪到别人身上,甚至将他的低音提琴视作一种障碍。这是这个小人物身上的悲剧所在。
这是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在《低音提琴》中讲述的那个“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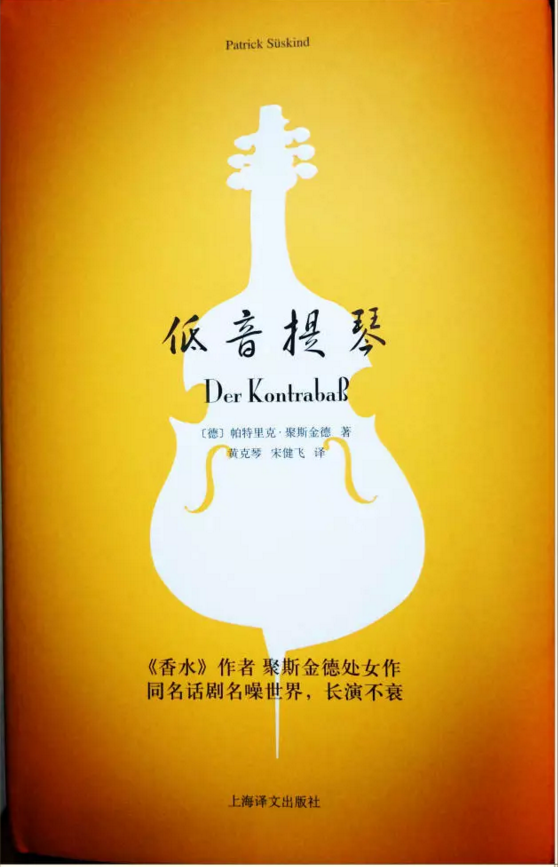
这个中年男人喃喃自语,充满了不平与愤懑。他认为不受人关注的低音提琴才是奠定了整个乐队的基础,低音提琴就像地基。他可以在暴风雪天气里,为了使低音提琴保持恒温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琴,而自己却因此染上了流感。但同时,他又将自己身边两年没有女人的原因怪罪到这把琴上,认为琴是阻碍自己恋爱的罪魁祸首。
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在他的自述中,提到了萨拉——同在一个乐团中的一位女歌手——他爱慕着她,“那位女歌手——她叫萨拉,告诉您吧,她有朝一日肯定会走红的”,以及瓦格纳——对他的评述则满是挖苦与讽刺。然而尽管他喜欢萨拉,却羞于表达,只在内心将这情绪进行无限放大和臆想,“我已经恋爱了,或者说心里已经有了相好的,我说不清楚,她也还不知道”;瓦格纳作为颇受争议的德国作曲家在“他”看来作为音乐家业务水平很差,除了弹一手蹩脚的钢琴以外什么都不会,甚至“还打老婆,当然是打第一个妻子,不是第二个”,认为“他自己也没法容忍自己,他那一脸的疙瘩完全是由于……恶心极了!”
书中他的自白中,谈到了大量音乐领域的知识,这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所谓艺术家应具备的常识,而另一方面,他越是想要卖弄他的音乐知识,我们在他的喋喋不休中却越能看到他的不平与不得志。当读者被曝于他那大段独白中,事实上很容易从中看到自身的生存现状,这个小市民将所有不平都怪罪于他人身上,这样的人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本书中,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低音提琴》尽管是聚斯金德的处女作,在戏剧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剧于1981年9月在慕尼黑首次演出后,后来许多剧院纷纷上演,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欧洲话剧舞台上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是最常被演出的单人独幕剧之一。一个人在台上大片的独白,不甘与痛苦,愤怒与责备,都靠台词和几个动作表现出来。因为太过简单而精确,就如同一把剑直戳入人心脏,毫不留情的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