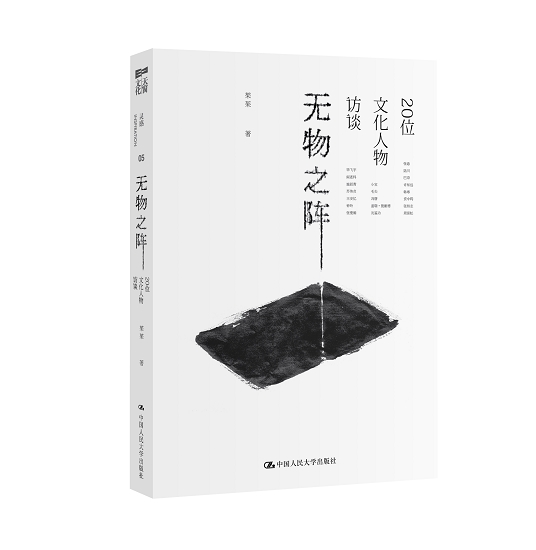应许之岛
2016年07月05日 15:24 倪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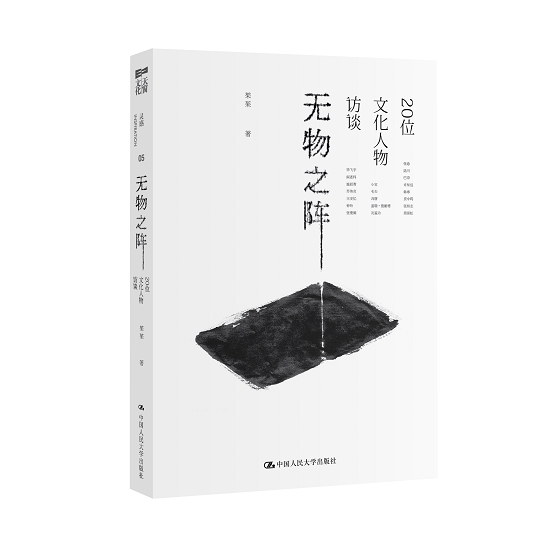
【八圈:这是左读右涮第79次广播。我们陪您从初冬至春暮,看文坛逸事,探名家八卦,吐出版圈的槽,流连全球的书店,并结合时事推荐值得一读的小文,以文章带出相关的背景书籍。我们用这样的平台,慢慢联结起了近700位读书的人。这700位朋友,不是互联网时代用来夸耀的用户数量,而是实实在在的,会拿起屏幕阅读的人。感谢每一位读到这段话的人,你们的每次阅读都是给这个平台的操作者以巨大的鼓励。】
【本文作者茱茱,原名倪婧,在杭州读本科,本科毕业后在我大滨江逡巡数月,后去香港求学并工作于香港媒体。采访了许多来往于香港的文人之后,集成《无物之阵》这本集子。本文是作者的自序。在眼前港岛多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陆港两地情势错综复杂之际,这样的一个视角,有助于我们对香港做另一种层面的观察,小心翼翼地接近它矜持的存在。
经作者同意刊发,侵权必究。】
旅途最惊艳的总是开端,所以我有时会羡慕旅游大巴拉来的一车一车的观光客,羡慕他们从高高的车窗向外张望的好奇眼神,他们大多头一回降临香港,这个光怪陆离的岛。一切都是新鲜的,等待着他们去打量和丈量,叫人念起每一个落地异国的时刻。
我把这座城市叫做应许之岛——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许其后代“流奶与蜜之地”,昔日的Promised Land,今日满目血腥动荡。香港这座Promised Island却幸运得多,历经战事、殖民与回归,他们与故去的时代立约,向不明的未来盟誓,这借来的空间,吊诡而华丽地跨过了世纪。然而岭南这块迦南美地所拥有的,却总是别人许给的安稳,也成了香港最大的不安。
新的总是好的。然而有一天你总会习惯这个城市街头巷陌的棱角,熟稔了攀山越海的门路,不由暗自惧怕磕碰的张力消失、城市的光晕变浅。所幸我永远乐得做个异乡人。“融入”始终都不重要。老旧餐室里百年不变的奶茶和菠萝油包,天花板上风扇的样式、地砖的纹路,与你抬头见到的电视里、上世纪TVB的场景似乎无太大分别。冲锋枪般的粤式调笑,干脆利落的男欢女爱未曾变过,变得只是愈来愈路人的明星脸庞。这是一座瞬息万变的国际都会,拼装都会的每个零件,日日以最高速运转,人们的目光死死盯向前方,暗地里却总给我以不变应万变的错觉,仿佛一种高度饱和后的缓慢,提供了另一种安稳,继而生出一种浪漫,让我这样的异乡人,心安理得停靠于此,选择做一个岛民。
常说岛民的天性是狭隘和不安,这两样最容易激起扩张和征服的野心,香港则把这种野性内化了,资本主义的鼻息如奶如蜜覆盖整座城池,无人能挣脱。架空人群的天桥,掏空城市的巨怪地下铁,灯火映天的商场,嘉年华式的橱窗,橱窗外川流着写满欲望的面孔。却别忘了岛民天然有守旧的天分,香港以最温吞的方式包裹了中西,这座应许之岛,倒成了很多人眼中传统与文化的庇护地。
城市的吸引力在于能够随时展开的想象,香港的过去藏在时间摊开的掌纹里,点线面之上,想象构筑起了时间立体的城墙。有了想象可以依附的实体,城市的灵光便不会消逝。而我想像的客体,很大部分依附于那些半世以来南来北往的文人客卿,小思老师那一辈人也许早已做过类似的功课,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香港文化地图:
从薄扶林道的港大校园一路往下走,许地山当年提着皮箱戴着礼帽来到港大主持中文学院,如今葬在薄扶林道的坟场。西环的海味铺,高高吊着咸鱼的尸首,透过玻璃罐里木乃伊般的海马与蜥蜴,怎么叫人想起张爱玲,眼见她一路搭叮叮车至中环,沿着石板街拾级而上,身后是浓重的夜色。中环士丹顿街13号,香港兴中会的旧所,着长衫的孙中山,后来化为电影中一个面目模糊的身影。又或者是北角的叉烧铺,倒悬着的皮肉焦黄分明的烧鹅,优雅的长颈垂落,竟念起年初离世的诗人也斯。搭天星小轮过九龙,尖沙咀乐道,日常寻觅米线和葡式蛋挞的后街,萧红和端木蕻良曾挤住在8号的小屋中,她在这座小岛写出了《呼兰河传》,死前留书“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火车至新界,清翠满山的中文大学,钱穆一手创办新亚书院,立起为故国招魂的大旗,暗夜里玄黑沉寂的吐露港,是我与这座城市情愫暗生的起点。
所以我喜欢鲁迅说的“菰蒲”,菰蒲是水生之物,旧时常指隐士安身之所。唐代刘得仁留诗《宿宣义池亭》:“岛屿无人跡,菰蒲有鹤翎”。以上所列的,都是搅动红尘的名字,却都有“梦坠空云齿发寒”的一刻,于他们而言,这座岛大概更似菰蒲,即便是不愿托终身的生死场,也是安身立命的庇护所。静夜暗涌的维多利亚港吞吐着历史,足以“尘海茫茫沉百感”。
存于想象中的历史,是城市的灵魂,抽掉灵魂的是死城。每念及此,那万古不变的幻象即刻被击碎。香港每天都在不情愿地变,香港人某种迫切的自赎,在旁人眼里成了焦虑和骄傲。外人对这座岛指指点点是最不明智的事,在她背脊密密麻麻的经络里,埋了太多的悲愤沉积和一碰就痛的敏感。也许她擅长自嘲,却不甘为外人所戳破。刻薄如鲁迅,匆匆路过,便一口指认“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和“默默吃苦的土人”。所以世故的人,不妨把嘴皮和笔头都放钝,用白描的方式讲述她。目下的香港人大概不得不承认他们所擅长的健忘,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浅水湾酒店早已倾坍,伴随着日日消失的摊档、食肆、鱼塘乃至海平面,还有搁浅了的记忆。高傲的南来文人和自暴自弃的香港人说,香港文化已死。回归以来,香港之变难以忽略,然而她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场域,不中不西的夹层中,不敕为思想相交缓冲的中站,文化在这里以一种诡谲的方式生长。身为局外人,目睹两岸三地各种现象在这座岛上的角力与平衡,时间越久,我越不敢用简单的语言一以概之,这座城市时时袒露出不同的面相,香港文化究竟在哪里?
既然想像由人而发,不如我们开始一种逆向回溯的当代想像,两年前因为一些机缘开始做人物访谈,既非专职,也就不为稻粱谋,竟然坚持至今。南来北往的客卿永远有,客居岛屿第五载,垂钓于时间之河,回头看我访问过的文化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岛民,却又与这座岛有或深或浅的勾连。他们多半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上一辈人中,又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人?有人是她的异乡客,有人背弃她远渡重洋,有人将自己的黄金岁月奉给她却又选择离开。更多的是匆匆过客,抽啖烟、歇歇脚,给我讲讲他们的故事。
所以,这座岛又有了新的想像。
旧日中环摆花街的顾绣店已经一间间迁出,不知施叔青是否在这里勾画了妓寨的招牌和黄得云的褻衣。摩罗上街的古董摊档,复刻的赝品在太阳下做着昨日异梦,钟玲曾和余光中的太太范我存结伴于此淘古玉?清水湾的云海,毛尖当年就在湿哒哒的乡愁里埋头写着一封又一封上海通信罢。港大庭院里的玉兰花香,替苏伟贞留存着一段死生恋眷的记忆黑洞。张曼娟也一定还记得这座随时可以穿山越海的小岛,和那只不时造访窗棂的老鹰,由這南国島嶼望向故土的距離,是古稀之年的高行健長長放逐的半生。总是在傍晚,行过西环夕照万丈的海,耳塞里张悬正在唱着岛屿生生死死的腐坏——云烟已过,岛屿依旧。
还有一些正在前行的想像,吐露港畔,我们依旧能看到范克廉楼的抗争海报和烽火台的辩论,一些未曾丢失的传统,守望着这座岛最难能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照本土社会议题和思潮走向,岛屿内外,更多的声音在此激荡,那些不安分的名字,本身就昭示着一种想像和应和。在看不清未来的浓雾里,想像本身就是一种前行的力量,也是岛民们给自己的许诺。应许之岛,正等待后来者赋予新的定义。
卡尔维诺的成吉思汗问马可・波罗:“同样是从偏远的地方归来,你却只会告诉我某人晚上坐在自家门槛上乘凉时想些什么。你的跋山涉水究竟有何用?”马可说:“不管我的话能唤起你对哪个地方的想像,你都会处在自己的位子上,作为观察家来看它,即使在皇宫里,也能看到木桩上建造的村庄,也能感到带有河口海湾泥腥气味的微风。”
一问一答间,我既是马可,也是可汗。访谈是一场旅行,我在陌生的岔路口迷路,向偶遇的路人打探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偷偷把自己的记忆和臆想编织进别人的述说。我也坐拥一座渡口,夜泊的马可向我叙述异乡的塔楼、天边的星辰,没有光亮的焰火,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在亦真亦假的时空拼凑起一幅文化地图,那是二维的岛屿,蜷缩在时代的一角。每个人说的都是自己的香港故事,香港的故事哪里能说完。我能有的,只是这幅小小的地图。
想书名是件头痛的事。早前在《野草》里读到鲁迅的“无物之阵”,不禁为这个意象暗自叫绝:“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文章写于一九二五年,隔了近一世纪,我们仍然被困在这无物之阵中。诚然,从来就不存在完美的年代和社会,每一代人都有需要与之对抗的现世暗面。先前布阵的,是先生檄讨过的体面的慈善家,学者,儒商;还有好听的道德,国粹,公义……到今日,敌人愈来愈多,面目愈来愈妩媚动人,我们或仓皇不知出路,或坦坦堕入蜜网。
最危险的敌人,无非都在构造美好的幻象,铺就隐蔽的利益链,驱使人为一扇门背后虚掩着的光亮飞蛾扑火。无需以害威逼,不用道德挟持,对资本权力的追逐、黑暗当前的沉默和犬儒,全出于自己的选择。在无物之阵中跳脚的,低头一看却是自作自缚,自然要心生惶恐和虚无;也有那不知低头的,走到对面成为布阵的一员,无物之阵于是代代相传。
所以最终还是决定偷来这个词,不好也不坏,隽永如时间。鲁迅是时代的叛徒,今天已经少有人愿意做叛徒——天地不仁、谋生不易,难为与时代为敌。就以访谈这等讨巧之事,记录下20位当代文化人的心境,倾听他们征途的来路,被缚的阵脚,对时代的希望与希冀——我们都将在无物之阵中老衰,你还是否愿意选择做一个战士,持着刺向现实的长矛,递与虚空的盾,在这无物当道的年代。
献给这所城市,这座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