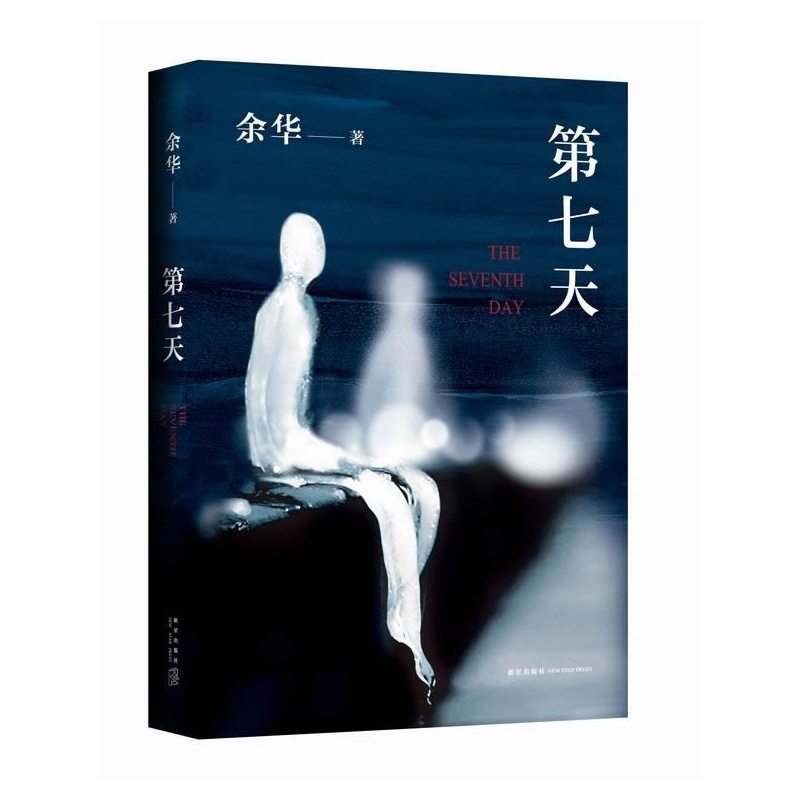意外之外
2016年07月05日 15:28 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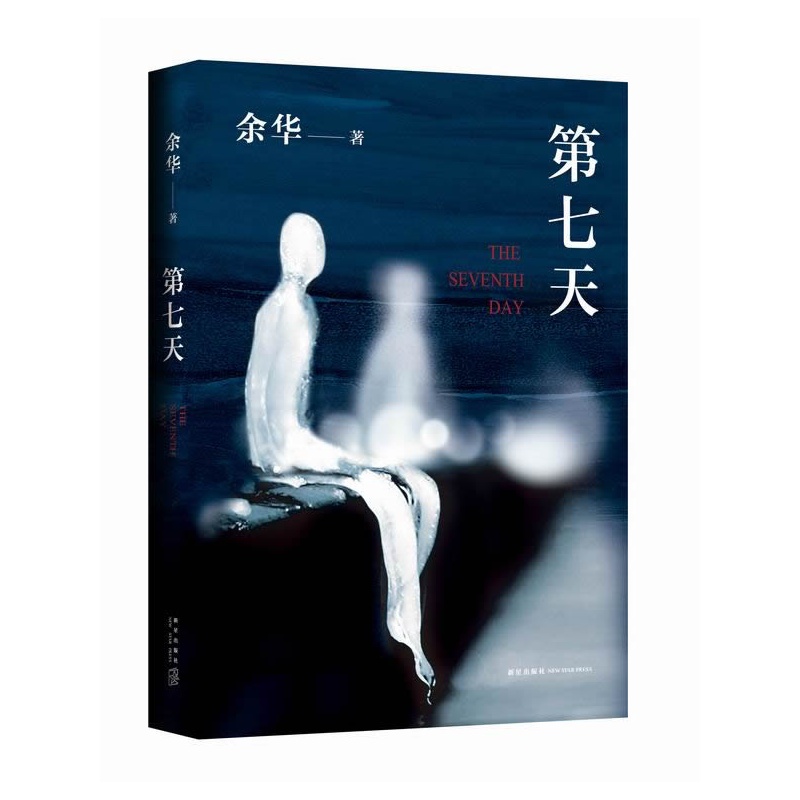
余华不止一次说过,他在写一部长得望不到头的小说,一部边缘人变得更边缘的小说。
后来,我终于读到了这本小说,如果说死亡是一种“更边缘”的话。跟读《活着》时的满目惊奇不同,《第七天》这本希望让人能惊而悚的小说却意外地没有“意外”。
如果这样一句话,在文学评论中有点刻毒的话,我希望余华兄能够原谅我。起码,他已经开始思虑死亡(或者说终极追问),思虑亡者与生者的关系,而且,以死后的“生活”作为写作的主体,在当代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其实,死亡是个重大命题,但是在中国,死亡被粉饰或美化,国人缺乏对死的敬意。
起码,余华在此处破题。
诺奖得主莫言已然让我感到失望,那只是用写作的品种和迎合的选题炮制出来的一种丰厚,那种丰厚里没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含量。而寄予厚望的余华,期待他捧出的是一个华贵的熔炉,然而现在的感觉是,我们正目不转睛,他却手下一个打滑……
好吧,他回归了稚气未脱的时代,在后中年向童年转弯。其实,《第七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死无葬身之地。这句话很符合e时代的微博体,更像冯(小刚)式幽默的贺岁片中的一句台词。
可以想象,离开了海盐的牙医生涯的余华,在首都享受着一位著名作家的荣华富贵,在世界各地边游历边宣传自己的作品,靠写微博就有人为他的世界杯之行买单……这样的生活,是如何地成就了他、幸福了他,更是如何地匮乏了他、毁坏了他。
这种空虚,就如同酒色对身体的一种掏空。
读了《活着》后的N年,我第一次见到余华真人,是余华的《兄弟(上)》刚刚问世的时候,百万稿酬的被炒作和高强度的写作似乎把他榨干了,他在杭州接受我们一帮文艺记者的采访时,脸色憔悴,就像刚经过长途跋涉。在回应我们的丢过去的一堆“炮弹”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他的头脑中的发条快速转动的声音,他颠覆了我对作家不问世事的一种幻想。那时,我天真地以为,作家的大脑是浸在文字场中的,所以不问世事才是仙的姿态。
但我依然要用“男人与男孩混合的气质”来形容他。他总是兴致勃勃,对这个世界和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作为作家,妖异与他绝缘,他显得心理过于正常,甚至可以用强大来形容。在余华的发展路径中,这种强大越来越大地将他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我问过余华,写《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哭,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终于悄悄说,后来通读修改时,用掉了厚厚一沓面巾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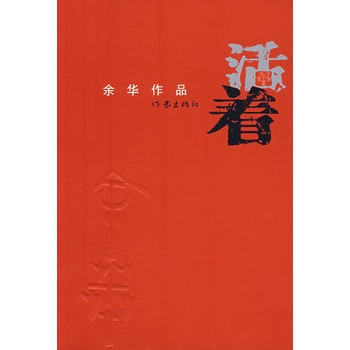
所以,《活着》是一部充满了意外的作品,因为它罕见地不抱怨,不贬损,而是告诉人们,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不需要超越或战胜。哪怕被生活虐得死去活来,依然保有一种珍贵的暖调,闪耀着辉光,鼓励读者在诡异的人生中继续走下去。
当我改行当上出版人后,跟余华愈发接近起来,出版了中国首部电子书《余华@》。在他的话题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了一种辽阔。他用一种社会学家的眼光和目力来审视中国和世界,用作家的细腻和叙述方式来看似嘲弄实则忧虑,起码我看到了一种滋养和一种秘而不宣的深情。
长久的等待中,我们期待着他贡献近年的行走和思考,期待着飞流直下般直抵人心的故事或者叙述。我们想读一读,没有被金钱侵染的文字和思想,是如何伸展出它的脉络和流动汁液;犀利的文风需要多少万公里的里程累积起来;看透世间的目光是如何历经岁月方能打磨而成。
我真诚的希望,余华兄的生活不要这么优渥。不,我并不认同恰如“江郎才尽”这样鲁莽的论断,我觉得他有,他可以,只要用一点苦楚酿造和触发他内心的敏感器,他可以十分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