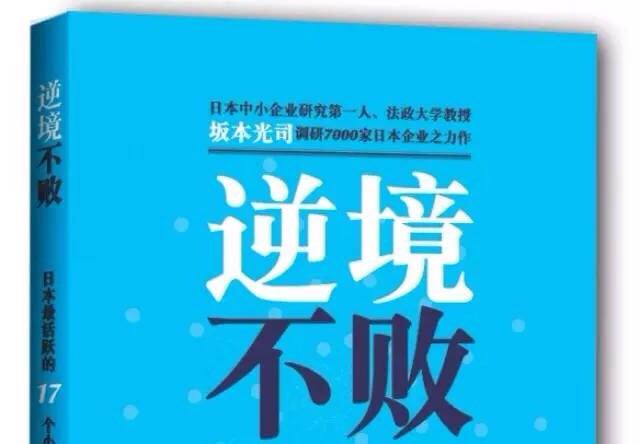我所见的日本企业
2016年06月15日 10:30 陈蔼婧
很早很早以前,大概是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是个老太太。就是那种你现在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的老太太,转发吃什么会得病,吃什么能延年益寿那种。约莫是个民族主义者吧,在课堂上,老太太经常穿插各种段子。类似这样的,比如“日本人来我们这里买花生,收了花生后把花生壳里面那层东西抽出来现场就能织成特别好的布再卖给我们,唉呀,把买花生的钱都赚了回去”。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日本人技术真高明。当然,老太太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夹杂着各种情绪的,褒贬不一。还有一次,老太太又说,日本人来我们这里开厂啊,每天早上老板都是第一个到厂门口,见到员工就鞠躬,每天早上7点啊,比你们都早,怪不得人家赚钱厉害。我们地方上因为和台湾的特殊关系,所以很早就有了个台湾投资园,老太太想必是以讹传讹,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段话。不过这段话却一直记下了,给我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振动。直到我真正编辑坂本光司的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有说老板每天早上迎接员工的。坂本教授可以调研过7000家日本企业的啊,如果有,他肯定会说,是不是?
可见,老太太也被人坑了。感谢这本书的特约编辑陈蔼婧提供的这份手记。
“我所见的日本企业”
读这本书的前后,我跟随一个项目组去华南作劳工调研,实地走访了两家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恰好都是日企。虽然企业的体量、生产内容、产销结合程度和坂本先生书中写的大相径庭,但日企独特的用人文化,眉梢眼角都透露出丝丝缕缕的相似,整个调研过程不断有“难怪如此”“果然如此”的弹幕在脑海里张牙舞爪。
坂本先生在书中所表彰的充满活力的企业的特征,以及后来所举的实例中,优待员工大概是最不容人忽视的一点。这点在调研中我也深有体会。劳资双方的矛盾无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其核心无非待遇二字。调研走访的日企,毕竟是外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其做到坂本先生书中所言员工第一主义不免过苛,但工会主导下的年度工资协商机制,员工代表在协商前对于所主张的工资涨幅,从CPI、房租乃至奶粉涨价各方面搜集、处理数据的能力,最后协商下的上涨结果,都是令我惊讶甚至是惊喜的。将可以预见的矛盾提前缓和、化解,在制造业企业用工荒的时代,真是高明。
受访的两家日企的基层员工,也都提到本企业员工辞职又回头的比较多,工作三年以上就基本不会再走。企业提供的免费日语培训乃至工会组织下的远程大专教育,参加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以后出去再找新工作,还是留在本企业升职加薪,学历都是加分项。能提供这些机会,并且让员工可以有足够的工余时间去完成自我提升的日企,大概都是秉承坂本先生书中所提到的“人才丰富”的理念吧。
我自己在调研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张贴在布告栏关于工资上涨的通知。根据国务院相关部委的规定,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两年调整一次。我去华南调研的时候,适逢该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而受访企业的工资标准和所在地市联动,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及时调高,连生效时间都是同一天。而企业所给出的基本工资自然又要比该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上那么一截儿,当然并不多,也就是几百块。规范,但比规范还往走一步,这一步大概就是日企文化进行在地化调整和成本控制后仍然对劳工保有吸引力的地方吧。毕竟他们在劳工市场上的对手,是很多连劳动法规定的基本项都无法保质保量完成的内资或者港资、台资企业。
我的父亲自己是个小型企业的管理者。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脱离国企,我从记事起到现在的二十多年,也是父亲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摸爬滚打的二十多年。他的书柜里放有好些翻译过来的日企管理经验著作,是我在网络未普及年代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我并没有和父亲当面交流过对于这些著作的读后感,但从书籍的折角和勾画中看到了消化的痕迹。
而这也是我对于本书在国内出版意义的期许。本书的读者和我的调研对象或者调研报告的阅读者,很可能交集并不大。而坂本所描述的日本中小企业的自救,在用工环境、国内经济形势都大不相同的中国,也并非可以榫卯结合似的照搬,但书中所流露出的管理智慧仍然让人感佩并向往。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哪怕只是调整之后的“规范,但比规范还往走一步”。当然,这也有赖于政府操作的进一步规范。

《逆境不败》
红旗出版社201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