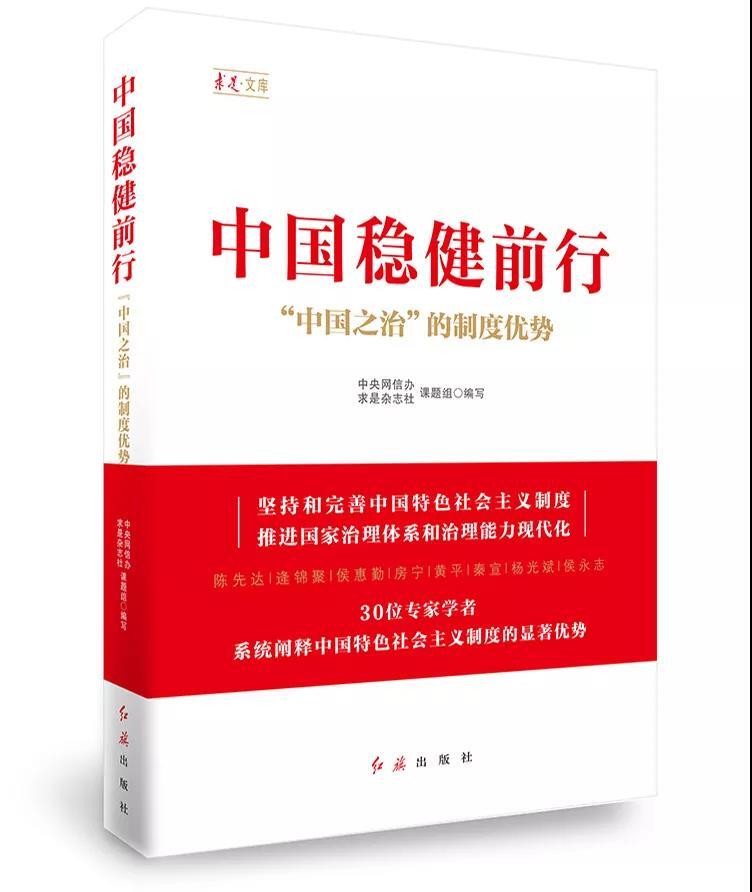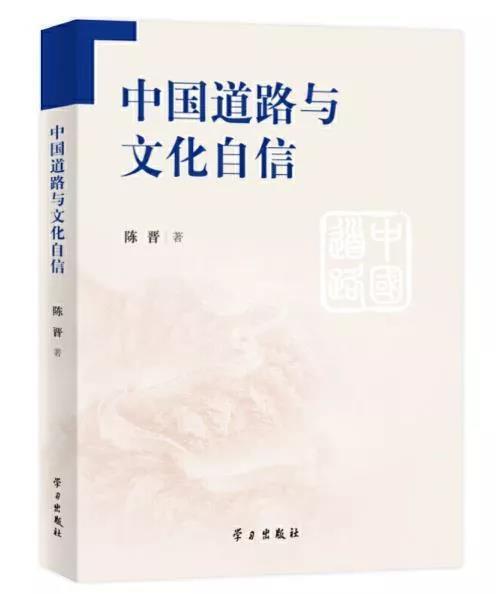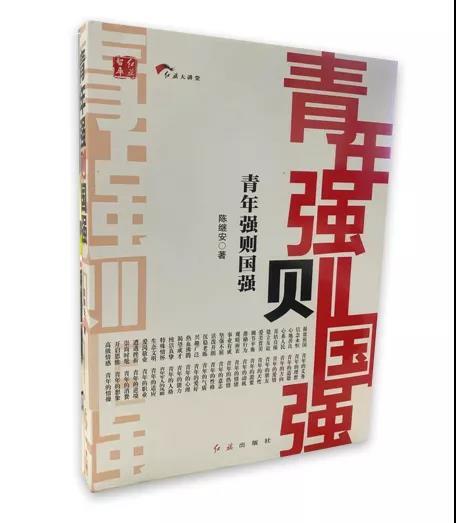《爱丽尔》:“钟形罩”里静默的呻吟
2016年06月15日 10:59 张阅

你再也做不了那黑鞋
我在其中居住,像只脚丫
一住三十年,一穷二白
几乎不敢呼吸,不敢打喷嚏

西尔维娅·普拉斯
后世可以轻松地说,西尔维娅·普拉斯是个有抑郁症甚至精神病的天才女诗人,于是她选择自杀。但无论是在1962年丈夫特德·休斯变心离去之前,她“每天早晨就像上班一样到借来的书房去,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写她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还是在分居后迎来几乎每日一诗的10月高产期,并在叶芝住过的公寓签下五年租约,灵感十足地继续写诗、定写作计划,我们都看不出生命力旺盛至此的诗人为何要在1963年2月11日开煤气自杀。这批诗歌,最后通通收入《爱丽尔》,整整齐齐如遗书般放在写字台上,等待世人阅读。
想靠近她,只能回到描述她21岁自杀事件始终的《钟形罩》和《爱丽尔》,两者合起来正好是她一生的自传。但诗却不好懂。可自白派的初衷不正是脱离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非个人化诗学”的主张,大声抒发自我情绪吗?以西尔维娅·普拉斯、罗伯特•洛威尔、安妮·塞克斯顿甚至艾伦·金斯堡为代表的自白派,对自己的出身背景进行最残酷、最疼痛的自我剖析,揭露自己最隐秘的欲望和幻想,以不可遏制的冲动告诉世界自己知道的一切。尽管如此,看《爱丽尔》,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在透明的钟形罩里不停捶壁,却听不清她的呼喊和呻吟。“我”字最难懂。
这样的诗,适合夜晚阅读,我们能放下戒备和心灵屏障,感性地接受她爆发的原始力量,她释放的讯息。它们充满对死亡、伤害、复仇的向往,久读会陷入狭小的迷宫,但这种浓重的负面情绪却有种纵身跳入死地而后生的积极感,犹如涅槃乐队狂暴又温柔、自毁又激进、妥协又复仇的音乐——主唱Kurt Cobain与普拉斯殊途同归地以死亡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神秘的力量感,恐怖而奇异的美感,在“爹地”和“拉撒路夫人”中最为明显,通读《爱丽尔》,这算是最易懂的几首。
很明显,诗人在“爹地”中攻击了父亲和丈夫。全诗有种悲哀、愤怒、仇恨和爱交织的复杂情绪,整体是一步步抛弃父亲和与之相关的一切,与自身的过去脱离关系,迎接新生。她父亲是1901年移民美国的德国人,与纳粹无关,却令她从小难以融入社交,二战期间,她的口音和出身,同学的反纳粹言论,都令她自卑,她一开始就有“生存焦虑”的隐患。“你再也做不了那黑鞋/我在其中居住,像只脚丫/一住三十年,一穷二白,/几乎不敢呼吸,不敢打喷嚏。”“黑鞋”这个意象有保护和限制的双重隐喻,代表了父亲对她一生的影响,也提及父亲致死的脚伤病。父亲在她8岁时去世,只留下贫困,她由此产生被抛弃感,而青少年时期对金钱和地位的意识和焦虑,导致她终生缺乏安全感——可怜她去世前还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对父亲的爱与恨同样强烈,本诗不仅声称她每十年一次的自杀是企图回到他身旁,“把我的小红心脏咬成两瓣的黑衣人”,还描绘了她与父亲在海滩的欢乐回忆和她企图让他起死回生的孩子气行为。
被丈夫抛弃,被评论家低估《钟形罩》,人在受刺激后召唤过去的悲伤记忆和感受,并非少见,普拉斯会把过去、现在、回忆、想象都糅杂到同一首诗歌里。“爹地”中,她的思绪被“父亲—德国—纳粹—犹太受害者—受害的我”这种自我折磨的联想占据。从“每个女人都崇拜一个法西斯”这句开始,父亲、休斯、纳粹的形象纠合在一起,犹如隔着毛玻璃的三重唱。意识流是普拉斯常用的创作方式。“生日礼物”从第一句“这是什么,在这面纱后,它难看吗,它美丽?”开始,像伍尔芙的短篇《墙上的斑点》那样,思绪顺势而下,同时“当我静静地做饭”又让诗歌沾上居家烟火气,思绪流到“最后的晚餐,医院的盘子”,读者立即感知到恐惧,果然,下一段就出现“你害怕了”——普拉斯对冷漠语气描绘血、医院、死婴、颅骨、死亡等等能造成恐怖震惊感心知肚明。从“我的拇指,而非洋葱。/顶端几乎全切下/只余一块铰链似的”(“割”)的惨状,竟一直顺流想到毁坏者(Saboteur)、神风飞行员(Kamikaze),跟上她的思维节奏,才能跟上她创造的美。
除了亲人,还有什么激发她“从灰烬中/我披着红发升起/噬人如空气”(“拉撒路夫人”)的仇恨呢?《钟形罩》似乎能成为解读《爱丽尔》的钥匙:她好胜心强,性格敏感,不放过新鲜事物,对社会新闻感同身受,对性关系有精神洁癖,厌恶成为男人的附属,厌恶沉闷乏味虚伪……甚至可能还有被男人强奸未遂的经历。普拉斯的仇恨向着整个世界的平庸与邪恶,她把万物转化为己身体验,又把私人经历普遍化为人类的经历。触目惊心的“申请人”,究竟是申请签证,工作,还是婚姻?“首先,你是不是我们的人?”提问者的咄咄逼人,很像强者对弱者的虐恋——照顾、强暴、改变、许诺一个更弱的弱者镜像。这首诗也展现她一些特别的押韵方式,句子因而产生韵律滚动感:相距不远的词压头韵或尾韵,同段末尾词重复,一个短句中对同一个词连呼三声,等等。朗读英文原句“你能说话,说话,说话”时,有力量感和压迫感。
她为求每段句数一样,语意甚至句子不写完便另起一段,在不讲究每句格律一致的自由体下有些奇怪,也为翻译带来了障碍。另外,《爱丽尔》中除了“波克海滩”是一组长诗,还有压轴的一系列以蜜蜂为主题的“蜜蜂聚会”、“蜂盒送达”、“蛰”、“过冬”可视为一组。以死亡为艺术的女诗人,写下“蜜蜂正翩跹。它们尝到了春天”的时候,是不是正要奔赴死后的“新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