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和握着一支什么样的笔
2016年06月14日 16:17 萧耳
1
永和发来她刊登在《收获》长篇增刊上的长篇小说《1979年记事》,吩咐说要我看了之后写点文字,因为我之前也给朋友们的书写过一些评论文字,她很期待我的评论,我不知高低深浅地,先是和她瞎聊一气,称她是女王小波,又天马行空地跳到说刘索拉写文革的寓言小说《女贞汤》,见永和兴致也高,又瞎扯八道地说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里的姐妹花和王小妮写文革的小说《1966年》。
我那股小聪明劲儿一上来,什么我都敢瞎谈乱谈,曾和建筑学专家聊建筑,也能把人家聊得以为我真懂,我以文学的修辞聊建筑,当然能让建筑学家听得觉得新鲜了,要不是后来要回到现实,跟永和说我要烧饭了,我还将扯扯陈冲导演的禁片《天浴》,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以上这般的半自恋半得瑟,只是为了衬托出我读完永和长篇《1979年记事》后的感觉:我真是悔不当初啊。跟海一样深不可测的永和姐耍小聪明,这不是自己找死的节奏吗!
2
永和,大名陈永和,福州人,在日本和中国两栖。她曾跟我描述过她多么喜欢北海道,但是现在到了冬天,为了生活的方便,永和还是会选择回温暖的福州猫冬。她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三坊七巷边长大的福州人,现在她写了个以福州为中心的地域背景的长篇,小说的时间背景是1979年,火红理想人见人爱的80年代还没有开始,文化大革命已经平息三年。

陈永和
这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基本上是文革年代个人命运的延续,或者说清算。永和小说里的那几个人物:我、儒谨、梅娘、我的表姐芳、关根,清算着清算着,全成了非常态里的人物。或死亡或疯癫或疯魔,是他们必然的命运。
3
荒唐年代,让人不疯魔不成活。连永和的笔也彻底疯魔了。我猜测这是我最近在朋友圈看到永和的照片,发现她忽然满头白发的原因。一个人如何这么不要命地写,完全豁出去地写,写火葬场,写神经病院,写停尸房,写遍地的老鼠,写人像狗,写人像猪,写人格分裂与歇斯底里,写乱伦与性奴……
永和,一个女子,之前她甚至也不是专业作家,要蓄积起多少力量,将自己的身体,锻炼成一个可以把一个鬼魅世界的一切都坦白出来的身体?
4
之前,某年夏天,在杭州。永和和我、柳营几个有一番长谈。我们是博友,微博时代来临之前的博客上意气相投的朋友:永和、半夏、念青、阿若、彦子、柳营、我,基本上都是女人,爱好文字的女人。我们把谈思想当件事件做,不错过任何机会,在上海谈,在杭州谈,在福州谈。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一群神经病女人,幸好,我们各自都被收留了,有了温饱,才可以傻傻谈思想。
永和来杭州和我们谈思想,几年过去,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一个观点:一切的行为,甚至你拥有的你的一切的思想,都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在长夜咖啡馆的漫谈中,永和总能自圆其说,我奇怪地看看,永和的身体也不见得有多强壮,欲望也不见得有多么的炽烈,凭什么永和认为甚至你的命运都是你的身体决定的?
现在,我看到了永和在小说中对这个“身体主义”论调的坚决贯彻,甚至我对她的过度强调,稍稍有点小意见:永和,你为了你的身体哲学,已经在向昆德拉看齐了吧。你从身体哲学出发,让两个阶级的对立也有了身体依据:工人阶级力气大,粗壮有力,能征服女人的身体。知识分子思想复杂,身体虚弱,只能征服女人的头脑。
所以,从小遭到继父性虐待的芳表姐,悲剧性地“身首异处”:她的身体已经只能适应野蛮暴力的继父,这工人阶级以“走后门”的性方式征服了芳表姐的身体,甚至她已经迷恋于他的性虐待。而芳的头脑中,爱的却是知识分子、有才华的作家儒谨。
她明白自己“身首异处”的悲剧,一生难以再获得幸福宁静,因而她痛恨母亲:正是因为文革中父亲冤死,母亲为了孩子的未来有个工人家庭的身份而嫁给了没文化的工人,却又内心高傲,宁愿被毒打也不愿意和工人阶级的丈夫睡觉,才让这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又“绝了后”的工人拿她的女儿当成了复仇工具。
他强暴自己的继女,一边痛骂她一边占据她的肉体,又故意让她五次怀孕堕胎。母亲最后在气恨交加中病死才得以解脱,而至死,女儿芳也不曾原谅她。芳的恨是:母亲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身体甚于爱惜女儿的身体。否则母亲可以为了女儿不再被性虐待而向丈夫低头屈服,但是母亲做不到。
是母亲一个“大小姐”内心的骄傲,毁了自己和女儿的身体,还有命运。而工人阶级继父的仇恨也比海深:只要已成为她妻子的这个女人愿意和他睡觉,他可以为她做一切,但是她,就是这么骄傲。
同样的身体与灵魂的分裂状态,在小说另一主人公,在关根死亡事件中受刺激发疯的梅娘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隐晦解读。读到这儿我有一些的疑虑:永和的“身体主义”是不是也是一种偏见?而她利用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次向读者“身体主义”的传道,那么读者是否会买账呢?至少我,对此还是持审慎态度的。
5
如果说永和在芳和母亲、继父三者关系和命运的处理上是触目惊心,那么追究到几位主人公在文革时期的林场苦难,则是令人发指了。
永和写那个后来成为省内知名作家的儒谨的苦难和被毁灭,一是讲了爱上梅娘的聋哑孤儿关根对他的折磨:干任何事都是戴着写上罪名的木牌子以示侮辱,这还是小事,更大的苦难是孤独的儒谨在被关的小屋中,只能与乌泱乌泱的老鼠为伍,甚至只能和老鼠做朋友。
对此永和是这样表达的:儒谨只有把自己也变成老鼠,让自己的心成为老鼠一样的心,他才能麻木了,才能活下去。一个只能把自己变成了“老鼠”的知识分子,他还会有正常的人生,正常地爱人吗?
永和还不肯放过可怜的,受尽了非人待遇,让人觉得医治他三生都仍然伤痕累累的儒谨,她安排“我”,一个火葬场工人,也是芳的表弟来到儒谨呆过的林场小屋,看到了从前属于儒谨的一本书上,在空白的地方写满了“老鼠”字样,以及画的老鼠,共有几千个。
够了永和,请你高抬贵手吧。关于老鼠与极权社会为背景的描写,我只在乔治·奥威尔《1984》中看到过像你这样入木的,极端恐怖的:“老大哥”的手下们,终于以放出一大群丑恶的老鼠,征服了一对异己者——之前对“老大哥”统治表示不满的知识分子恋人。那个细节,曾让我非常难过,甚至恶心,而永和的几千只老鼠,表达的却是一个文革中受到非人待遇的知识分子最深层的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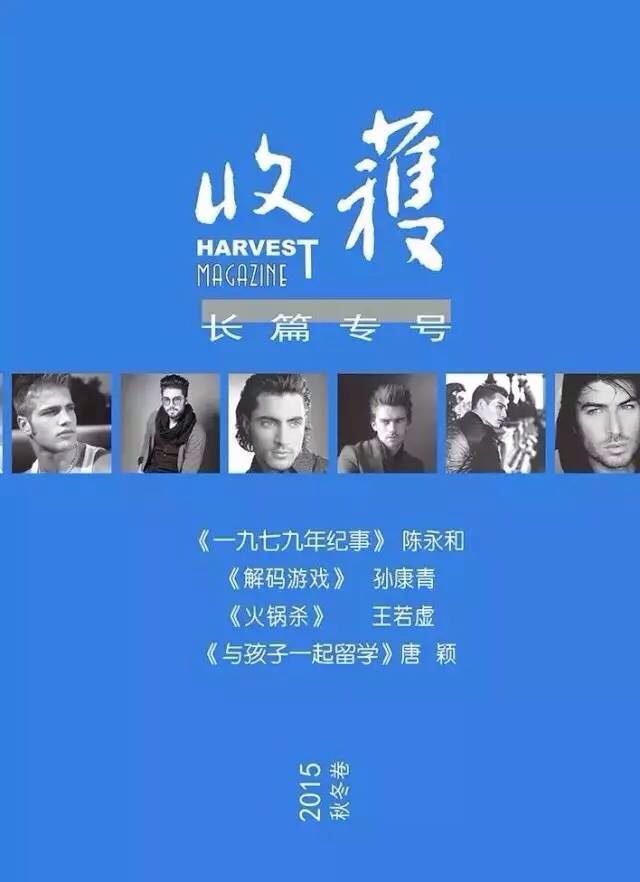
2015《收获》
长篇专号
6
读《1979年记事》,我认定了永和有一个雌雄同体的身体和脑袋。世界上有两种作家,男作家和女作家,男作家未必喜欢女作家写的东西,女作家也未必喜欢男作家写的东西。伍尔芙认为自己是雌雄同体的,所以她写得出《到灯塔去》这样的意识流杰作,我以为毕飞宇也是雌雄同体的,所以他笔下的女人是女人眼中也真实的女人,但很多作家,比如男人写女人完全是意淫式的不着调,女人写男人也是隔靴搔痒的多。
但永和的身体了得: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我”,后来留学去日本的“我”是男青年,而且是火葬场员工。从“我”的视角望出去,火葬场和停尸房成了叙事的主要地点。如果说《入殓师》是温情脉脉的,那么永和关于火葬场的相关叙述却是若无其事的。
若无其事中,又显出怪诞,喜感的一面,永和就这样像个会怪笑几声的女巫,穿越了生与死的界限,让死亡这件严肃又令人有些害怕的事,也以一种与荒诞年代完全吻合的怪模怪样,回到了世俗。这就真的有几分女王小波式的戏谑味道了。否则,怕是永和也担心这样的小说过于沉重了吧。
7
在文革背景下,永和开始挖人身上的动物性。因为从身体主义出发,人和动物在永和眼里,也是可以越界的了。人有时变成动物性,动物有时变成人性。永和借人物的话说,芳的妈妈和继父,就像牛和鸡,本来根本不会碰到,不会交集,但是一场文革,让他们的命运纠缠。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样。
仙女一般美丽的梅娘,和爱慕她的聋哑人关根也一样,本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是美丽的梅娘被乡党委书记强奸,生下孩子的孩子被关根送了人。
爱着梅娘的关根终于向他效忠的干爹开枪,使自己走上了绝路。又因为关根与梅娘精神上,身份上的不平等,一方面,被关根看管的儒谨更加受难,一方面,关根自愿装成狗,学狗的样子成为落难的梅娘身边独特的“忠犬”一般的存在,关根从人降为狗,就像“降维攻击”,使善良的梅娘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
关根做得好“狗”,却做不好“人”,所以他不了了之地死了。他的死,给梅娘、儒谨几个已经极为坎坷的知识青年的命运雪上加霜,使他们还要背负沉重的良心枷锁。
永和写了关根身上的“狗性”、儒谨身上的“鼠性”、芳表姐身上的“猪”性,分别指向身份、政治、性对人的三重异化,这时候的陈永和,我以为是文学大师们附了身。她已经写得没有任何界限,没有任何禁忌,性与死,全不在话下,她真的有一颗强大的心啊。
8
我发现我也一直在说身体。最后再说一下身体,我发现生于永和的那个时代的人,和我们这些文革后生人,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缺的正是那么强大的,有容量的内心和身体,像永和,平静如海面,激越如火山。
大约是1976年,我幼年有一十分模糊的印象,大约是1976年,我亲眼见过革委会这样的地方,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被抽皮鞭,嚎叫着,我相信这个记忆是真实的,而非从影视剧中移植而来的。
我想我是庆幸的,没有在这样一部小说面前狼狈逃跑,读这样一部小说,你就当炼一炼自己灵魂的承受能力吧。我是分三次读完整部小说的,因为我的身体太过脆弱,吃不消一次读完这么令人发指的文革故事。
9
我也怕得罪人,就不说陈永和的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之前写过文革题材的哪几位大咖作家们了。永和提供的内容,故事,已经让我这读者忘了小说的技术性层面,觉得那些东西简直是浅的范畴的东西。
10
永和的灵性在于看上去的朴拙。看上去淡淡的永和,其实浓到了极致。她是一座到了知天命之年才开始爆发的火山,永和的身体内里拥有岩浆的质地,如果你怕烫,就只好与她保持一点距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