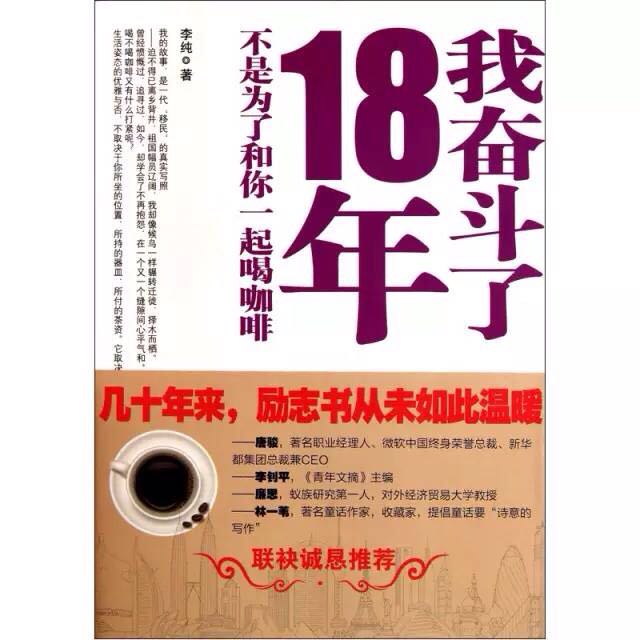十八年&一杯咖啡
2016年06月13日 14:35 红旗出版社 含一
近期被刷屏的国产电视剧《欢乐颂》,第一季虽已结尾,围绕这部剧的各种评论却是余波未平。这部剧乍一看一点像国产版的《欲望都市》,五个个性、职业迥异,来自不同阶层的女生被编剧安到“欢乐颂”这个大上海的中档小区,构成一个小社会。这部看似时尚的都市剧,引起的现象级的话题却不是那么时髦和轻松——阶级分化和阶层固化,编剧也被猛批“三观不正”。先看看编剧为主角们安排的人生:华尔街金融精英安迪,一路开挂的人生,一众男神为她倾倒;目空一切的富二代曲筱绡,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金钱和关系摆平,还是成功的创二代;颇有姿色、深谙世事的樊胜美,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却最终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的拖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关雎尔,如愿通过考核,成为大公司的正式员工,继承了父母的中产地位;邱莹莹成了咖啡网店店长,从小城下层变成了都市下层。故事似乎在昭示:阶级差别不可逾越,底层群众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阶级的桎梏;而精英阶层从来都是人生赢家。 到底是编剧太残酷还是现实太残酷?群众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是努力奋斗就可以改变命运吗?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便是我和你的最大差别,根深蒂固的分歧、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在于此。我曾经以为,学位、薪水、公司名气一样了,我们的人生便一样了。事实上,差别不体现在显而易见的符号上,而是体现在世世代代的传承里,体现在血液里,体现在头脑中。”曾看过《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北大清华农村生源仅一成寒门学子都去了哪》,“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这两天又有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在湖南农村长大的中国小伙何江,成为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华人学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当然,他也补充“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到底是编剧太残酷还是现实太残酷?群众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是努力奋斗就可以改变命运吗?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便是我和你的最大差别,根深蒂固的分歧、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在于此。我曾经以为,学位、薪水、公司名气一样了,我们的人生便一样了。事实上,差别不体现在显而易见的符号上,而是体现在世世代代的传承里,体现在血液里,体现在头脑中。”曾看过《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北大清华农村生源仅一成寒门学子都去了哪》,“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这两天又有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在湖南农村长大的中国小伙何江,成为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华人学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当然,他也补充“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认为唯阶级论、唯出身论、阶层固化论,是错误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拼爹拼妈不如拼自己”,道理自然是没错的,可是这个社会似乎没有给这些没有任何资源和背景的年轻人太多的机会和选择。樊胜美、邱莹莹在剧中未免有些被脸谱化、“污化”,但是他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年轻人的缩影。而何江的例子也从侧面说明寒门学子取得一些成绩是极其不易的。年初的时候,“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的话题刷爆了朋友圈,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虚假新闻,可是这个话题何以掀起了如此巨大的舆论风浪?就是因为这个话题既涉及“富人”,也涉及“穷人”,涉及“门当户对”、不同阶层,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代入。当时很多城里人尤其是上海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这个上海姑娘,不遗余力为她辩护。有人评论“这本质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价值取舍,以及他们的梦想、愿望和追求。”说白了,就是富裕阶层希望自己的财富、地位、阶层能巩固、延续。其实阶级分化和阶层固化不单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日本甲南大学经济系的森刚志副教授曾对日本的富翁进行访问调查,出版过《日本富翁研究》一书。并对富翁的妻子做过问卷调查,发现她们有两大特点,一,学历高,二,都是出身富裕的家庭。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早就有社会阶层固定化的趋势:富裕的父母让下一代得到优质的教育,结婚的对象也要求门当户对,大多来自同一阶层。结果,富裕阶层的资产越来越多。在日本,无论是哪个时代,像好莱坞影片《麻雀变凤凰》里那样,社会下层出身的女性被富翁看中而结婚的可能性非常低。写到这里,又想起一本书《我奋斗了十八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一位年轻的女性作者写的,挺励志,也很适合年轻人看。作者也许是为了和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构成呼应。二者并不矛盾,只是角度不同,一个强调的是社会分配的不公,一个突出的是奋斗的价值。阶级分化和阶层固化是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的进步去改善,当然也需要不同阶层的人参与。对于每个出身平凡的普通人,奋斗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阶层、实现人生飞跃,至少可以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毕竟,上升是艰难的,下滑则太容易了。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认为唯阶级论、唯出身论、阶层固化论,是错误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拼爹拼妈不如拼自己”,道理自然是没错的,可是这个社会似乎没有给这些没有任何资源和背景的年轻人太多的机会和选择。樊胜美、邱莹莹在剧中未免有些被脸谱化、“污化”,但是他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年轻人的缩影。而何江的例子也从侧面说明寒门学子取得一些成绩是极其不易的。年初的时候,“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的话题刷爆了朋友圈,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虚假新闻,可是这个话题何以掀起了如此巨大的舆论风浪?就是因为这个话题既涉及“富人”,也涉及“穷人”,涉及“门当户对”、不同阶层,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代入。当时很多城里人尤其是上海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这个上海姑娘,不遗余力为她辩护。有人评论“这本质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中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价值取舍,以及他们的梦想、愿望和追求。”说白了,就是富裕阶层希望自己的财富、地位、阶层能巩固、延续。其实阶级分化和阶层固化不单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日本甲南大学经济系的森刚志副教授曾对日本的富翁进行访问调查,出版过《日本富翁研究》一书。并对富翁的妻子做过问卷调查,发现她们有两大特点,一,学历高,二,都是出身富裕的家庭。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早就有社会阶层固定化的趋势:富裕的父母让下一代得到优质的教育,结婚的对象也要求门当户对,大多来自同一阶层。结果,富裕阶层的资产越来越多。在日本,无论是哪个时代,像好莱坞影片《麻雀变凤凰》里那样,社会下层出身的女性被富翁看中而结婚的可能性非常低。写到这里,又想起一本书《我奋斗了十八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一位年轻的女性作者写的,挺励志,也很适合年轻人看。作者也许是为了和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构成呼应。二者并不矛盾,只是角度不同,一个强调的是社会分配的不公,一个突出的是奋斗的价值。阶级分化和阶层固化是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的进步去改善,当然也需要不同阶层的人参与。对于每个出身平凡的普通人,奋斗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阶层、实现人生飞跃,至少可以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毕竟,上升是艰难的,下滑则太容易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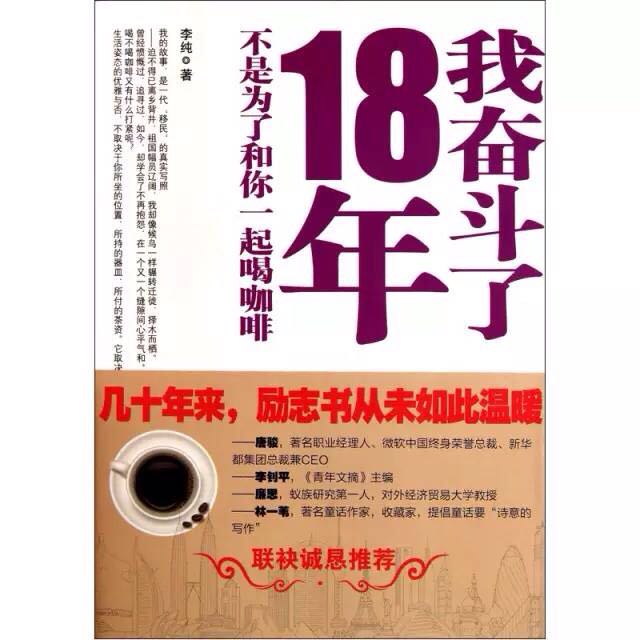 《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你一起喝咖啡》李纯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10-1
《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你一起喝咖啡》李纯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