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文学评论
2016年06月13日 14:51 李俊洁
读张直心《晚钟集》中的文章,常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不自觉地放慢阅读的速度,因为珍惜每一个字。这样的心情只有在我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会有,如珠如玉,回味无穷。而张直心是评论家,理论化的批评文字却能令读者着迷兴奋,感觉那些文字穿越时空,与被评论者神魂相契,又与读评论者赤忱相见,是他的魅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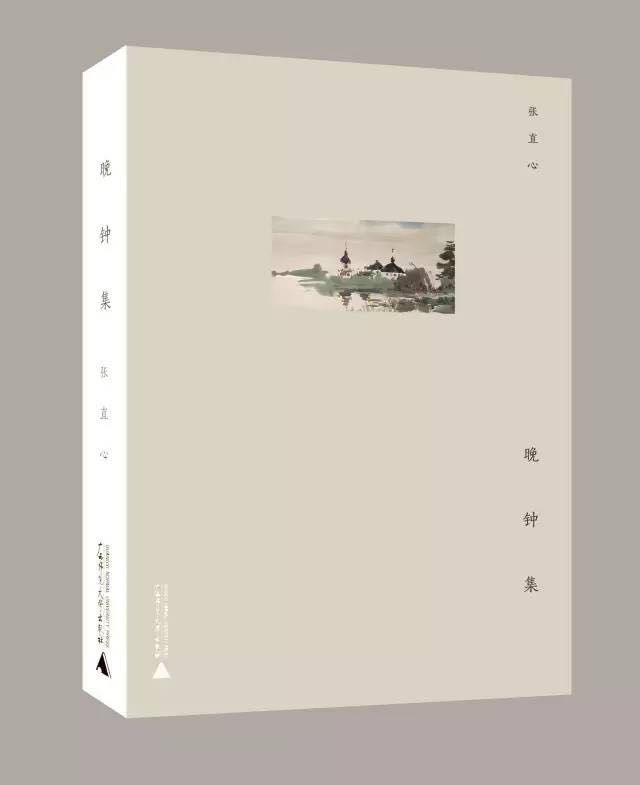
《晚钟集》张直心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2月出版
他是谦谦君子,做人作文都有那种过去学者的风度。他写他的老师蒙树宏先生:“‘正统’,但能理解异端;严格,却对年轻事物很宽容;平实,却不无孤傲地拒斥着平庸;冷峻,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热烈。”其实倒是他自己很好的写照。不事声张,只默默成全;谦逊低调,却自有执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张直心未必认同自己是儒家,但他有类似的气:眼光追随着大家如鲁迅、托尔斯泰,敢于直面大问题,不畏艰险,也不避敏感话题;同时对于“弱势群体”,如无名的青年作家,鲜有关注的边地文学作品,仗义执言,倾力扶持。这个“义”与其说是拒强扶弱,不如说是本着“诗心”的一视同仁。他的笔尖有担道义的责任感,也有体察灵气与诗性的审美力,两者构成了文本独特的精气神,有厚度,亦有温度。
他用“石薪”这样朴实低调的笔名,文字却第一眼就可以让人惊艳:极好的节奏与韵律感,华丽,却不是浮于表面的修辞,而是骨子里的盛情。这种文字的气质让人想起的是那些几代传承的贵族,事实上他也确实出身世家,见过大繁华,也走过大动荡,他的批评遂有不一样的底色:表面上理性精准地解剖着,内里却丰沛绵延地体贴着,在那些评论他人作品的跌宕起伏里,有着切肤的荣辱兴衰感。
他最好的几篇评论,几乎都是在困境里、在负面评价里替人翻案,在矛盾挣扎中悉心体察作者被压抑的诗心与生命力。比如评艾芜写于六十年代初的《南行记续篇》:
黑暗的社会,究竟有何“旧”可“怀”?作者苦苦追怀昨日的风景,社会的黑暗未曾使其黯然自伤,却因常感染着边地自然的神奇而萌生“怡悦的诗意”;作者多方“打听一些赶马人、偷马贼、私烟贩子的下落”,岁月淘洗,他却留下了那些被主流历史拒斥的边缘人“性情中的纯金”;心的荒凉处,幸得有边地那汩汩无尽的爱的温泉的滋润;“漂泊”这一不无象征意味的行为中,作者十倍百倍地领略了人性的自由、生命的销魂。隔着三十六年历史烟云往回看,原乡在时移事往中不仅生出一份忧伤,更生出了一份美丽。至此,我们读懂了,令艾芜神往的南疆,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主义新边疆,不如说仍是那文化学定义下的“边地”;而作者之所以袭用“忆苦思甜”情节结构模式,潜意识中正是为了赢得不合时宜的“怀旧”抒情的“合法性”。
又如评鲁迅《二心集》里强化文学阶级功能的话语风格:
鲁迅对《二心集》型话语形式明快畅晓有余、“深刻性不够”之局限并非无所觉察,一度仍不得不用,乃是出于强化政治宣传功能的功利目的。一旦鲁迅颖悟“弄政治宣传,我到底是不行的”,一旦他不愿再被“纯粹利用”、指派为“导师”一类的话语角色,潜在的美感定势便自然会引领他重新寻求个性化的深刻言说。
他不仅仅在读一个作家的某篇作品、某个切面,他所读着的是整体的生命力。不仅仅是盛景顺境时,也在被侮辱被损害时,在被压弯或变形后。他的评论,透过作品里时代和人生的沉浮起落,捕捉着某种本质的东西。这种生气、挣扎,一路行来的轨迹,是身而为人,是超越时空而属于全人类的悲欢。正因如此,他可以在极细微的地方敏感到极深邃的情味。
读多了张直心的评论文字,不难发现他有一抹区别于其他评论家的异彩:特别能捕捉一种野性的、蛮荒的、原始生命力的美,甚至于他的文字本身也跳脱一般意义上文人审美的趣味,而渗有一种边地文化的鲜亮与野性。
这种野性是能够跳出“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的调和之外,引导读者欣赏到“他不时想用臀部撞击嘎诗,让嘎诗品尝他的男子汉气魄,可嘎诗却灵活得像只机灵的野兔,左左右右避开了他的撞击”的血气的好;也是摆脱诸多评论日渐僵化、西化的坏风气,给文字注入活泼泼生气的好。这不能不说与他曾在云南边疆插队与生活多年的经历有关。
这段经历再结合本身的文字功底与学术素养,使得他在笔涉云南,笔涉边地文学时,能轻松跨越看不见的藩篱,游刃有余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他的《“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云南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最后的守林人》诸篇,美得摄人心魄!某种意义上早已逸出经院派学术研究的边界,是让人读了脸红心跳的,写给边地这个第二故乡的瑰丽情书。
这,才是文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