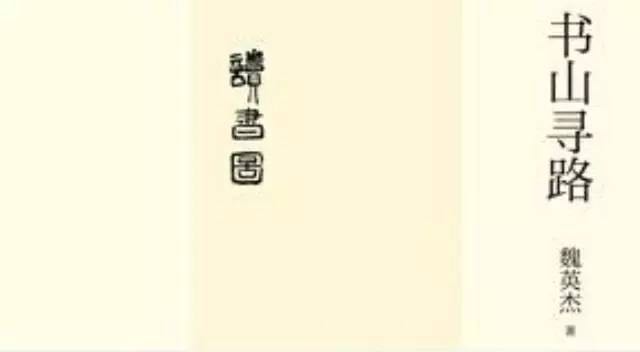魏英杰的读书之法
2016年06月13日 16:08 西木

我与魏英杰兄大约相识于七年前,那会我还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他已然是全国知名的时事评论作家。虽然如此,他却没有“知名”的架子,常与我探讨一些读书上的问题,令我受益良多。一次偶然的机会,听闻他从十六七岁开始做读书笔记,至今已有好几十万字,惊愕之余,便有一睹为快的想法,无奈机缘不巧,只读过当中的一些篇幅,始终未曾全部读完。
近来又听闻,他出了新书,便是这本《书山寻路》,选取了他诸多读书笔记中的精华之作,分为“知人论世”“见微知著”“思想之旅”和“命运之境”四个部分集辑成册。细细翻阅此书,从这些理性却不乏优美的文字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爱书人的阅读之路、思想之旅徐徐在眼前铺展开来,实在是美不胜收。
很明显,英杰兄是个读书有道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常与我说,读书之法有二。其一是构建框架,先从读史开始,为自己的阅读领域寻出一条线索,然后按图索骥、由此推彼,开拓出自己的阅读领地。比如,他建议我,若想读哲学,便可以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不仅能帮助了解基本的哲学术语和概念,更可以此为线索,寻得哲学领域的大家名著,系统全面,事半功倍。
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阅读方式,才造就了英杰兄“知人论世”“见微知著”的功力。从一个作者或一本书,甚至只是一个点出发,却能高屋建瓴,引出对这个作者的全面评价,或是一个学术领域的得失分析。在我看来,若无广博的涉猎,是万万难以做到的。比如,他从孔飞力的《叫魂》一书管窥海外中国研究的现状,便是一例。
又比如在《平庸的恶: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中,英杰兄探讨了“平庸的恶”这一由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是如何在国内被误读和滥用的。他根据自己对阿伦特著作的理解指出,“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匮乏,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恶”指的是广义上的邪恶,或者干脆说是助纣为虐式的作恶,而不是一般职务行为或失德言行。鉴于此,他认为将“the banality of evil”翻译成“平庸的恶”固然没错,但究其内涵而论,更准确的翻译是“恶的平庸性”。以我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的理解来看,英杰兄的论断当是十分有道理的。能在如此短篇幅的随笔中,将一个复杂的概念理清晰,且提出自己的见地,并不容易。
其二便是带着问题去阅读,由一个问题牵扯出一堆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先找准一个入口,勇敢地走进去,然后随意地沿着其中的任何一条支线行走,走着走着,便自有一片开阔的地域会展现在眼前。比如,他因看到朱大可在《神话》一书中考证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西王母其实是印度大神显婆的译音,觉得这些结论不可思议,便有了求证的心理,随对上古神话和考古学发生兴趣,就循着这条线,读完了李济先生的《中国早期文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及从考古发掘成果介绍华夏文明起源的《何以中国》和从文本研究来讨论中国古代王朝兴替的《世袭与禅让》等等。
如此读书之法,在这本文集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实在令我受益良多。叔本华说:“不加思考地滥读或无休止地读书,所读过的东西无法刻骨铭心,其大部分终将消失殆尽。”无疑,英杰兄的读书之法,是可以帮助我避免陷入这糟糕境地的。
当我看完他描述自己阅读《基督山伯爵》一书时的那种痴迫切、煎熬和痴迷的阅读状态后,我不顾严寒,毅然从被窝里爬出,冒着零下八度的严寒,打开电脑,买了一本电子书,迫切地看了起来。我想,这就是阅读的魅力,也是一个读者对另一个读者的信任。在我看来,人生之路千万条,读书不啻为一条安全且幸福的阳关大道。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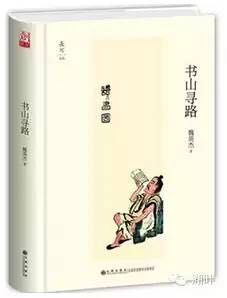
作者:魏英杰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年: 2016-2
页数: 256
定价: 42.00
装帧: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