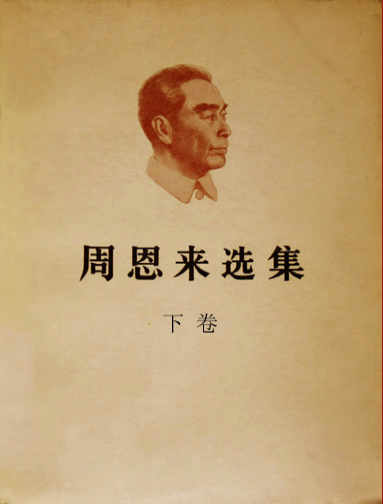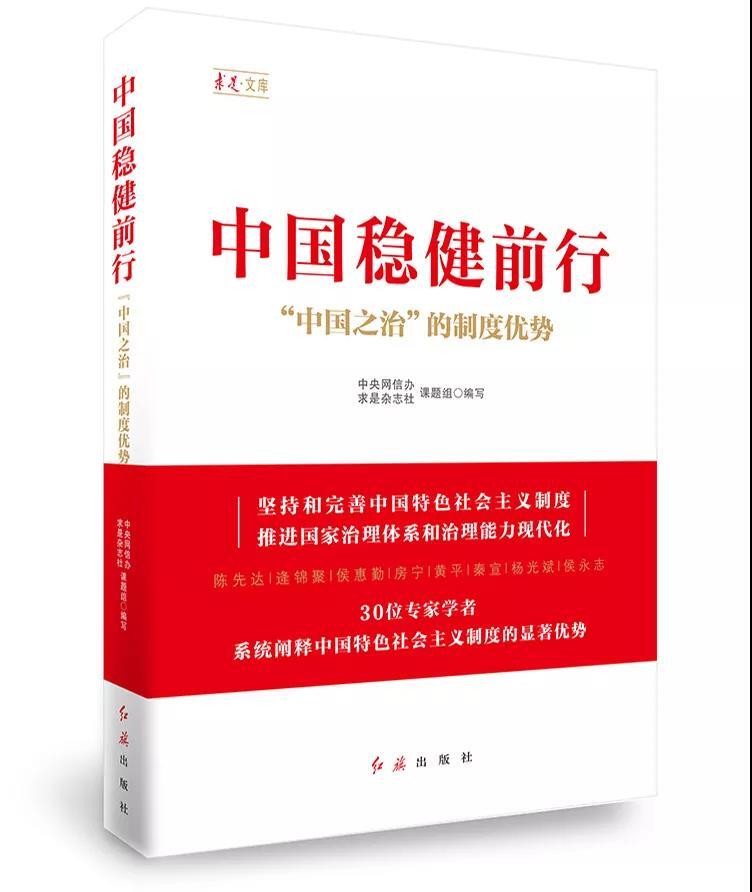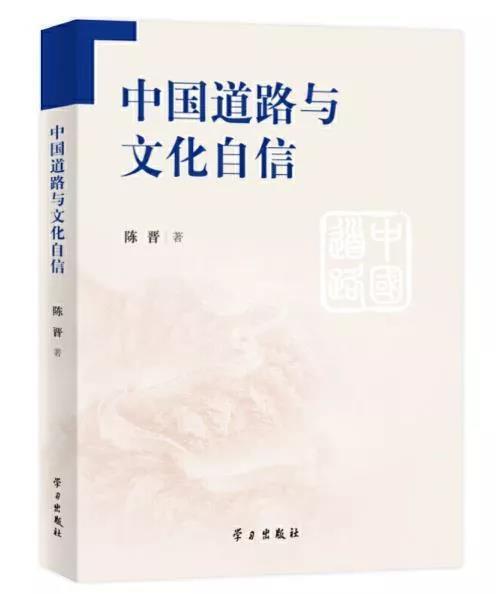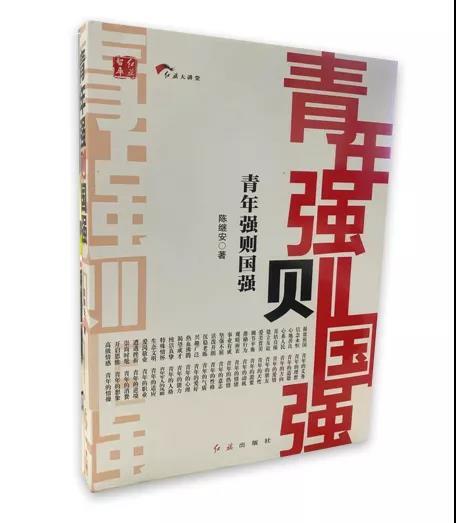《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2016年10月08日 11:10 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选集》下卷
二 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